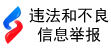刘邦坤小小说小辑(小说)
来源:昭阳信息网 更新时间:2007-01-04 17:04 作者:刘邦坤 责任编辑:
古寨人
这里的公路似乎很难称作路了,大坑小凹,愁肠百结,在泥浆的掩盖下又危机四伏,险象环生。车非常小心地走走停停,仿佛搏斗于波风浪谷之上的一叶孤舟。速度慢,我便有许多时间向外面观看。古寨其实还算是一个美丽的村子,公路的两旁是影影绰绰的绿村和房屋,远处是平坦而肥沃的稻田,有一条小河在田中间悠游而下,河水清澈透底,映照着更远处的青山绿水,感觉还真是不错。但公路却叫人十分恶心,淤积的泥浆平均厚度不下一尺,车一过则辗得向两边飞溅,路边房屋的墙上门窗上便厚厚地糊满光怪陆离的图案。村中间居然还有一条小街,人们十分自在地在泥浆中做买卖,也有许多漂亮的姑娘用手提着自己美丽的裙子,如梅花鹿一般在泥浆里轻捷地走动。我实在难以理解这些公路为什么就不能得到最基本的维护,我更难以理解古寨人为什么就能容忍它丑恶地躺在自己家门口。
返回的时候,我搭乘的是客车。同行的有几个刚从山里调出的老师,他们的行李捆在车顶上,箱子等杂物放在坐位中间的过道上,回家的喜悦和离别的伤感充满整个空间。车里于是显得非常混乱和拥挤。车刚要走、又来了六七个民工,他们自称是古寨人,扛着行李和钉钯板锄钢管炮杆等一系列杂物。车上的人便怂恿司机不要搭。民工听见,就大声吵闹:“我们是买过票的!哪个敢不搭?”司机见车里实在太挤也劝道:“车票我退给你们,今天实在坐不下,你们明天搭货车来算了!”一个民工便撇了撇焦黄的虎牙,嘿嘿冷笑道:“明天搭货车也要得,但今晚我们的饭钱店子钱哪个出呢?”其他民工似乎觉得这话很幽默,全都放肆地哈哈大笑。司机见没办法,只好低声下去地请人们挪一挪过道上的杂物,民工们便七手八脚把自己的东西往车里顺,那些冰凉而泥污的东西一上车,压迫着人们不得不尽可能地收缩自己的身体,然而大家的心里都有一种刺嵌入肉中的感觉,烦躁而憋闷。民工们一窝蜂涌上车,车里自然没了座位――这类车售出的票只能作为上车的凭证。他们也不失望,嘻嘻哈哈地说着粗俗的笑话,一屁股坐在自己的东西上,其中一人见地下有只箱子,顺势一挪便坐到上面。一个老师说里面有东西,坐不得。民工依然坐着不动,老师再说,民工嘻嘻一笑:“坐一下咋个了?”有两个老师便勃然大怒,双手一拍大腿站起来,嘶着嗓音大吼:坐一下咋个了?坐烂东西哪个赔?哪个赔就站出来!”边吼边把手指朝前指着。车里顿时一片死寂,气氛就有些剑拔弩张起来。这时,一个民工便讪讪一笑过来圆场,说不准坐就算了,出门在外,脸红脖子粗的没意思。坐箱子的那个也将身一扭坐到地上。气氛终于缓和下来,车也叮叮哐哐开始走动,民工们随遇而安地坐在自己的工具上,一会儿又粗俗地互相开起玩笑来。道路在山间弯弯屈屈地延伸、枯瘦的太阳痴痴地嵌在天上,四面的大山上长满蒿草,越发显出分外苍凉,耳边又总响着那些叮叮哐哐的声音,直弄得人昏昏欲睡,似梦似醒。突然,一个民工大声喊:“东西掉了!停车!”车摇头晃脑地停了下来,几个老师便出去查看行李。一看之下,不由得叫苦不迭。原来绳索被抖松,已有三捆行李被甩下了路边的悬崖,崖底隔路面十几米,光秃秃的无可攀援,几个老师无计可施,直急得搓脚捻手。民工们便七嘴八舌出主意,后来就取出他们带着的绳索,拴住一人的腰慢慢放到崖底,再拴住行李一件一件地向上吊。下去的人最后被吊上来,早已弄得花嘴花脸。老师便非常感激、忙掏出“钓鱼台”抖脚抖手往民工们嘴上塞,民工叼了烟,嘴却不饶人:“
刚才坐一下箱子你们还鬼喊呐叫!要不是我们,东西还不完蛋?”其他人便哈哈大笑,直笑得老师们脸红耳热,嗫嚅无语。
硬币
“从今天开始,谁也别想再赊欠一分钱了!”乡村医生老李从黝黑的搪瓷口缸里喝口浓茶,扯扯披在肩上的衣服,心里又狠狠地念叨了一遍。
这是一个晴朗的赶街天。老李看见太阳从对面的大山顶上钻出来,那些红艳的光芒像鞭子一样抽打着山间呆头呆脑的白雾,白雾被赶到了远方的山洼里,山腰的村落渐渐清晰起来。羊肠般的山道上,赶街的人正蚂蚁一样慢慢地蠕动着。老李回头瞟一眼屋里火塘上煮着的针头,开始慢条斯里地收拾起地上的一堆草药来。老李一点儿也不忙,他知道山道上的那些人还远着呢。一个人在乡卫生院下设的这个医疗点上呆了都快七年了,他对这里的环境比对老婆的身体还要熟悉。
想到老婆,老李的心里又有些不安起来。他家住在山那边的坝子里,常年在山里工作是顾不了家的。年迈的父母和两个儿女都靠老婆一人照顾呢。昨天从家里返回时,老李把这个月的工资交给了老婆,老婆小心地数了两遍,说咋这么少呢?家里可又得买化肥、添小猪了啊。老李解释说:“前几天和单位结了帐,病人平时赊欠的医药费全部从工资中扣清楚了。我都一笔一笔地记着呢,山里人踏实,有了钱时他们会来整清楚的”。老婆哀怨地瞅他一眼,说这么多年咋不见哪天整清楚呢?天知道你在外面做些什么啊?老婆揉揉眼睛,眼泪就三颗两颗地掉下来了。老李斥责说:“你这婆娘只会嚼舌头哩。”嘴里在骂,心却软了,老婆可是个好老婆呵,她对丈夫的误会让老李越发内疚起来。
“从今天开始,谁出别想再赊欠一分钱了!”老李狠狠地下了决心。
一到中午,老李就忙起来了。山里人的病痛也像人一样喜欢凑热闹呢,每个赶街天老李都要忙个不停。突然,一个女人闯了进来,女人背上背着个孩子,嘴里像马一样呼呼地喘着气。她们显然走了长长的一段山路了。女人刚坐稳,外面又连滚带爬跌进一个瘦小的男人来,男人喘息着说:“李医生,快,快请你救救娃娃吧。”这时,孩子已经躺在女人的怀里了,两眼紧紧闭着,呼吸显得很急促。老李伸手摸摸孩子彤红的额头,惊叫一声,“哟,这娃娃咋烧得这么厉害呢,都火一样地烫手了。得输液才行了呢。”老李又翻看了一下孩子的眼皮,摸了摸脉搏,在一张空白的纸上匆匆开起处方来。开好处方,他又顺手挪过那架漆皮脱尽的老算盘,瘦长的手指头把那些珠子拨得哔哔驳驳地东躲西藏。老李抬起头,看了看那个瘦小的男人说:“要二十八块九呢。”瘦男人火烫一般的跳了起来,嘴唇抖了半天,说:“我们只带了二十块钱。李医生,请你先救救娃娃,欠着的钱过两天我们一定还给你。”老李摇摇头,果断地说:“不行,你们去找人借一下吧”。抱孩子的女人一开口就带着哭声:“求求你家了,李医生,再耽搁这娃娃怕不行了,我们真的没地方借钱了。欠下的几块下场街子我一定送来赔你,求求您了……”老李听不得女人的哭声,他的眼里有些模糊起来。老李眼睛一模糊就看见了老婆充满哀怨的眼神,看见了老婆正拉着手推车吭哧吭哧地在大路上走着,车上堆满了一袋又一袋的化肥……老李又摇摇头,小声说:“不行的,上级都有规定了呢。”老李一急,就不知怎么的编出了一句谎话。说着谎话,他的脸上热辣辣地红起来。
“妈耶――”这女人怀里的孩子醒过来了,是父母哀求的声音惊醒了他。他舔了舔焦灼的嘴唇,眼珠轻轻地转了转。一只手抖抖索索地在身上摸起来。孩子慢慢伸出手,说:“妈妈,钱!我有钱”。他的小手在母亲的眼前颤抖起来,“叮铛”一声,一枚硬币掉在了地上。硬币不安分,在地上打着旋儿,闪射着一圈又一圈银色的亮光。
老李叹口气,伸手摸了摸孩子那槽污一团的头发,小声说:“你这个娃娃呵……”然后就在一个笔记本上歪歪扭扭地写上“张三娃,欠八元八角五”。接着便翻捡出一大堆针水来。
浴室
小城俯卧于黄褐的土地之上,周围是一些田地和微微起伏的丘陵,其间点缀三三两两蚁穴一般的村庄,仿佛一幅荒寒萧蔬的清人山水。小城的建筑失于规划,卫生状况也很差。一年四季,街道总像洗不干净的脸,病恹恹的缺乏生气。风沙又大,大风起时,飞沙走石,日月惨淡。即使没有风,汽车后面也会腾起长长的灰尾,宛如慧星一样横扫而过,此时处在“慧尾”之中,感觉便很像一粒被掺了沙土暴炒的板粟,憋气,燥热,在大锅里跳来跳去却无可逃避。总之,小城酷似一颗旧衣服上的塑料纽扣,显露着一种破败而又瑰丽的色彩。
或许正因了这风沙,小城就有了许多浴室。浴室的布置大抵都很简陋:一间屋子像公共厕所一样隔成许多空格,每格之上设输水管道和莲蓬头等物。讲究一些的才用彩色塑料布为每个格子挂上门帘,也算有些保护隐私的意思。
我很喜去东门外一家名为“沐尘”的浴室洗澡。我欣赏那个典雅的名字,欣赏那种远离闹市的宁静以及天窗上射下的真实的阳光。在阳光下裸露身体会格外坦然。一个夏天的午后,我又去那里洗澡。站在莲蓬头下,任温润湍急的水流冲刷着我,好像粗砺的大手在温柔地抚摸,那种感觉舒适而又满足。我正在陶醉,突然被外面的骂声惊醒,一些愤慨的女声像冰凉的水蛇在浴室里乱窜:“……出来!不要脸!烂货,公然烂到这里来了!……”我掀开门帘一角,将头伸出去察看,浴室的门大开着,管理员正扶了门框愤愤然大骂,也许是考虑到进入男浴室的诸多不便,所以虽跃跃欲试却终究不敢造次,只是高叫:“出来!不要脸的。你出来!”我估计浴室里大约是进来了一个什么女人,管理员正在除魔卫道,而且我也突然警觉到某个格子发出一些细碎了声音,间或也夹杂着男女低声的碎语。一颗颗伸出帘外的脑袋全露出兴奋莫名的神情,都等着看一桩风流故事如何上演。小城虽不乏灯红酒绿的流言,厕所墙上也经常贴满离奇的怪病,可对突然发生在身边的艳事,人们依然新奇而振奋。这时,管理员的男伴来了,他大踏步走进浴室,用低沉而富有威慑的声音说:“出来!”一个格子的门帘终于很不情愿地掀起,钻出一个女人,裤脚和衣袖卷得老高,衣服地完好地穿在身上,再一细看,人们不禁吃了一惊,这女人头上已是白发飞扬,一张脸仿佛中药柜里贮存的一粒大枣,沟沟豁豁,皱纹密布,年纪恐怕已接近花甲,早已过了色彩斑澜的岁月。在众多的目光注视下,老女人显得十分局促和羞怯,她抖索着嘴唇,嗫嚅着:“……我,我男人……手是断的。他哪年就想,想洗洗……我帮他擦,擦身子……”仿佛是为了印证她的话,她身后的帘子轻轻一动,探出一颗苍老而疲惫的头颅,带着一种既歉疚又无可奈何的神情久久地伸在外面一动也不动。
乡村班车
那天要回学校,我在路上等班车。顺着那条年轻的柏油路缓缓朝前走,看着路旁陈旧的房屋,苍老的树木和秋收后疲惫的田野,看着没有鸟雀的黄昏和用单车驮着铛啷作响的饭盒回家的人群,我无端地觉得惆怅。是深秋了,一切都预告着一个严酷季节的来临。对于秋天,很多人都赞美她的成熟和充实,这是不必说的了。我是农民的儿子。农民对秋的豁达常使我感动,他们不会为一年的丰收沾沾自喜,自然也不会为秋风秋雨而感伤,拄锄立于原野,披衣行于阡陌,身旁有牛马无声地咀嚼,他们便是整个秋天了,这是天人合一的境界。面对父辈的博大,我常会为自己的敏感浅薄而愧怍。
走出将近四五公里,又有三个小伙招手。车停下却不上,只在前头同司机闲扯,一方说四块,一方说两块,夹缠多时,终究不能达成一致。司机便边开车边自语:“杂种,两块还不够你爹的刹车费。”片刻,又有人拦车,方式和结局一如前面三人。司机终于忍不住了,猛然将车发动,弄得车咣啷咔嗒一阵乱响,片刻后又环顾左右断然说道:“杂种!这些杂种。我认得是逗起闹的。哪天在城里我整给他瞧!”我站立于一个拥挤的角落,几次刹车的颠簸让我头晕脑胀,不知何处又突然涌起许多奇臭的油味,我不禁肠胃一阵翻腾,泛泛欲呕,转眼便有了晕车的感觉。
接着,又上来一个年轻的女人,背一个娃娃,提一个大包袱,左挤右挤才在人缝里站住脚。娃娃却醒了,哇啦哇啦地哭。女人将钱递给卖票的小伙,补回一元拿在在手里,却又连声叫司机莫开莫开,将头探出窗外,大声喊:“妈也――拿着!赶场天吃碗凉粉。”车外的老人却死活不要,说我有我的你留着用。你来我往,耽误了许多时间方才接了。车里早有许多人催促说快点快点,天都要黑了。
晚秋的山常常面目模糊,原因是多雾。傍晚时分,这雾便和着暮色蠢蠢地涌动,时空便粘粘糊糊地显得滞重而昏沉。在夕阳与黄土间,在漠然的绪风中,倏然传出“妈也――”的一声喊叫,空气不由得一震,这震犹如池中的涟漪,竟也是一层层地向四周扩散开去。那雾,那山,那夕阳也都朔朔地抖了几抖。一时间,我仿佛回到了儿时的村庄。暮色四合,炊烟袅袅,田野的上空便响着“妈也――吃饭了――”“狗儿哎――来罗――”的呼应,拖得很长的尾音在草尖上,树干间绕来绕去,历久不散……
卖烧洋芋的女人
卖烧洋芋的女人坐在大街拐弯的墙角,金色的夕阳温润地铺洒在她瘦削的身上,她的头发糟污一团,在晚来的微风中瑟瑟飘动。一只竹篮,竹篮里装些个头匀称、体型长圆的洋芋。半只铁锅,铁锅里几砣油黑的柴炭在歪歪扭扭地冒着青烟,炭火里躺卧着几个金黄的洋芋,竹篮边摆放着装辣子面的饮料瓶,外加两只简易得不成形的小木凳,这就是她的全部家当了。
大街像一条冬天的河,车辆和行人静静地流淌着。她的生意很清淡,但她不急,她知道:这里前面有全城最大的车站,后面有高耸入云的酒楼,左右全是红红绿绿的舞厅和发廊,一到黄昏,她的生意就会特别好做。那些背着包的旅客,那些细腰马蜂的女子,那些信步乱走的男人都会被烧洋芋的香气吸引过来的。生意清淡,卖烧洋芋的女人却没有闲着。她弯下腰,一手柱在地上,一手稳住炭火,眯了起皱的双眼,拢圆乌黑的嘴唇,“噗――噗”地吹着炭火,淡青的烟雾在她的头上一阵一阵地浓郁起来,卖烧洋芋的女人又开始不停地翻烤火里的洋芋。烧洋芋很讲究技巧,先要用猛火烧起锅巴,边烧边用小刀轻轻刮削,直至洋芋被烤得金灿灿泛着黄光,然后用中火烧透,放在火边烘着。吃烧洋芋的人很挑剔,既不能夹生,又不能烤得太粑。卖烧洋芋的女人一边忙碌,一边在心里算着账:昨天卖三十斤洋芋,赚了十六块五,看今天能不能卖到四十斤?算着算着,她忽然就莫名地恐慌起来,她掠了掠鬓边的乱发,揉了揉昏黄的眼睛,向两边大街的远处望了望,她招呼依在栏杆上看书的一个七、八岁的小男孩:“娃娃唉,给我盯紧点!别只顾看你的书。”男孩恼怒地瞅女人一眼,嘴里含混地应答一声,又低下头看他的书。男孩穿一身洗得泛白的暗绿的校服,显然是什么学校的学生,他拿在手里的是一本花花绿绿的语文书。女人又抽空看了看依偎在栏杆上的孩子,目光渐渐地有些爱怜起来。唉,这娃儿也该添件衣服了她在心里说。现在这学费咋就恁贵呢?她想,一学期咋就要四百多,三个娃儿就要一千多块了哩,地本来就少,种什么东西又不值钱,苹果两三角一斤,白菜七八分一斤,种一年还卖不够学费钱呢!一年里柴米油盐、人亲来往,总不能不用钱吧?卖烧洋芋虽说脏是脏点,又有城管的人来东撵西撵,可总比挑沙灰强吧,挑沙灰苦累不说,黑心的老板还常常不给钱,又不安全,河对门的张老三,去年从三层楼上跌 下来,至今还拖着一条断腿哩。卖烧洋芋的女人心里想着,不由得又叮嘱孩子一句:“盯紧点,娃娃。城管的人都来过两次了呢!”孩子不抬头,依旧看他的书。
黄昏来临,街上闲游的人渐渐多了。卖烧洋芋的女人生意慢慢好起来了,她手里麻利地刮削顾客选中的洋芋,嘴里利索地侃着价钱,洋芋刮好,用一把窄而长的小刀把它竖着剖开,刷刷刷地用饮料瓶撒上一层辣子面,然后合拢来递给顾客。卖烧洋芋的女人手里虽然忙着,但心里却非常高兴,她洋芋一般土黄而泥污的脸上微微地笑着,眼边的皱纹愈来逾显得深黑,白亮的牙齿在咧开的嘴里忽隐忽现。突然,一支壮硕的大手一把抓起竹篮,顺手将半边铁锅放进竹篮里,端起就走,边走边大声喝斥:“已经警告过你两遍了,你硬是不走!个个都像你这样,我们还咋个工作?”原来是城管的巡逻车开过来了,女人的家当全部被城管人员没收了。卖洋芋的女人一下子惊得目瞪口呆,气急败坏地一把揪住看书男孩的耳朵,嘶哑着声音大骂:“你这个花包谷哟,砍脑壳的绝儿子哟,叫你盯着点盯着点,你却只是看你妈的羞书!”男孩在女人的手下拼命挣扎,嘴里大声地哭喊着……
端着竹篮的城管人员不知为什么竟呆在了车前。卖烧洋芋的女人趁机窜上前去一把抢过竹篮,一手牵了孩子,飞一样地向一条小巷奔逃而去,她们崎岖而扭屈的影子像惊慌的小蛇在彩色的磁砖上乱窜,一晃就倏忽不见。
标语
张老者正蹲在巨大的房屋浓荫里吧嗒吧嗒地吸蓝花烟时,一辆颜色嫩黄的小面包车嘎地一声停在了他的背后。车上跳下四五个人,眼睛直往张老者家新建的那座砖房上瞅。张老者心里咯登一下紧张起来,他搓着手走上前去,嘴里咕咙说,这房手续全哩。一个戴眼镜的小伙扭头看了他一眼,却只顾和其他人说话,他说这墙还真是平整呢,写条标语可省不少力。张老者凑上前去说,我这房是新建的,这墙都才刷好哩,糟蹋了可惜。戴眼镜的小伙转过身,两只眼睛躲在玻璃后面警惕地眨了眨,老者,我是青山乡教办的主任,他说,我们可是在宣传“两基”工作哟,知道不知道,“两基”工作是政府的大事情,人人都有责任呢。
张老者听得带懂不懂,也不好细问。小伙些七手八脚已动起手来,年青人就是麻利,张老者两袋烟刚抽完,一条红艳艳的标语已经写好在他家的山墙上了,雪白的墙壁、鲜红的大字,张老者觉得还真是有些好看。小伙些抹抹手,歪头脑壳端详起他们的劳动成果来,其中一人忍不住大声念了一遍,扎扎实实搞好“两基”工作,青山乡教办宣。其他人大声叫好,然后就上车走了。
又一天响午,张老者的蓝花烟刚点燃,一辆蓝色的面包车又嗖地开到他家房前,车上下来的人张老者认识,是以前在村里教书的黄老师,听说现在也当了教办主任。黄老师说,老张,这标语是谁写的?神情语气都有些严肃,很像村里支书催公粮时恼怒的样子。张老者紧张起来,说七八个人哩,估着就写上了。黄老师叹口气,唉,老张呀老张,你回去翻一翻户口册,你可是咱绿水乡的人呐,你这房子正是交通要道,写标语正好,你咋个就让青山乡写了呢?黄老师说完就吩咐身后的老师,刮掉,我们重写。一个老师眯眼看了一会,说,黄主任,要不咱们改一改落款就行了?黄老师眼睛一亮,说你小子还真聪明。刷刷几下,“青山乡教办宣”改成了“绿水乡教办宣”。
又一天下午,黄色面包车又开到张老者屋前,几个小伙骂骂咧咧就要去改标语,张老者慌忙上去阻拦,说我是绿水乡的人哩,这标语就写绿水乡罢。眼镜主任张口就狠狠批评张老者,你这老者,“两基”工作是多大的事!你知不知道,在全市、全省、全国都是全民动员,人人上阵的啊,分什么青山乡绿水乡?也不听张老者罗嗦,小伙些三下五除二就把“绿水”改成了“青山”。
又一天,蓝色面包车又开到张老者房前,黄主任狠狠批评了张老者,叫张老者看守着标语,不准人再改,要他为绿水乡“两基”工作做一点力所能及的贡献。黄主任离开时“青山”又改成了“绿水”。
到了星期六,张老者在城里读初中的小儿子回家来了,见他爹一天愁眉苦脸地守着墙上的标语发呆,便细心地问了缘由。了解了情况后,小家伙皱着眉头想了想,突然眼睛一亮,抬条凳子垫脚,刷刷刷几下就把“绿水”二字刮个干净。张老者正在目瞪口呆,小家伙已跳下凳子,高兴地说,爹,这下不用看守了。张老者半信半疑地不作声。忐忐忑忑过了好几天,果然再也没人来找麻烦。以后,张老者逢人就慨叹:唉,还是识几个字好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