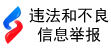枪伤(枪伤)
来源:昭阳信息网 更新时间:2007-09-18 08:57 作者:赵清俊 责任编辑:
鹅毛般的大雪,飘飘洒洒,纷纷扬扬。沉寂的村庄粉妆玉砌,透露出圣洁和一尘不染的气息。陈三拄着拐杖,像一只白色的笨熊在雪地里步履蹒跚,“三只”或深或浅的“脚印”瞬间便被雪掩盖得没了丝毫踪迹。一拐一瘸的陈三离村庄越来越近,一步步走向家,走近温暖,走近令他梦中揪心而朝思暮想的家。刺骨的寒冷穿透陈三的五脏六腑。陈三裹了裹军大衣,兴奋而激动,热血涌动却万般愧疚。父母是否安康?兰花的心是否安在门槛上急切地盼着自己的归来?陈三越想越害怕,却不得不去想。
陈三顺着七弯八拐的小巷走到了家门口,心却跳得厉害。陈三的心跳抖落了身上的雪花,陈三翻滚涌动的血液融化了冰天雪地。陈三调整了一下七上八下的心跳,跺了跺脚,抖了抖身上的雪花。陈三一声大喊,爹,娘,兰花,我回来了。陈三的喊声震得门前老槐树上的雪花一堵一堵的滚落下来。屋里传出几声狗叫,算是对陈三的应答。“你找哪个?”一个男人罅开门缝,伸出半张冷冰冰而疑惑的脸问道。陈三顺势一推,忘记了受伤的右脚,重重的一跤跌在堂屋正中。坐在火塘边的女人吓了一跳,惊得合不拢嘴。“你走错门了吧。”女人说。“兰花,我是陈三,你不认识我啦!我终于回来了啊!”借着微弱的灯光,女人看到了一块熟悉而又陌生的脸。女人张开双臂扑向陈三。旁边的男人呆若木鸡,模糊的脸扭曲得变了形,脸上的肌肉在昏暗的煤油灯下不停地跳动,心里明白了一切。女人弯下腰,扶起地上的陈三,满脸的泪水。“爹娘呢?”陈三问女人。屋里静得出奇,雪花落到瓦片上簌簌的声音把寂静推向了极致。兰花没有说话,丰满的乳房托着似乎要往前落下的头。饱胀的乳房似乎在急剧地膨胀,把兰花的头缓缓地撑起,兰花的眼神在两个男人模糊的脸上游走,紧张而担惊受怕的样子。
“爹娘走了!”兰花说。
“咋个走的?”陈三一声大吼。
陈三把手伸进怀里摸了摸,拿出一把冰凉的匕首,手一挥,深深地插在了方桌上,一道冷飕飕的寒光在昏暗的屋里飘荡摇曳,毛骨悚然,令人不寒而栗。陈三一声大吼,你狗日的给老子滚。站在门边的男人嘴唇蠕动了几下,望望兰花,叹了口气,无可奈何的模样。陈三又是一声虎啸狼嚎般的大吼,你狗日不想活了。男人全身像打摆子一样不停地颤抖,漠然地看了女人一眼,拉开门,迈出了门槛。一股强劲的风涌进屋子,煤油灯摇曳了几下,灭了。屋里一片漆黑,伴随着一阵急促的咯吱声,男人瞬间被风雪卷得无影无踪。兰花扑向门口大喊,黑二,回来。回来,黑二。黑二……喊声里带着哭腔,泪水被冷风打落。狂舞的雪花和肆虐的劲风吞噬了兰花高一声,低一声,长一声,短一声的喊叫。陈三握紧的拳头松弛了下来,冻僵的双手疼痛无比,在热血中跳动的心凝固在雪夜里。陈三脸上跳动的肌肉像大风过后的湖面恢复了平静。“爹娘是咋个走的?”陈三抬头看到堂屋正中爹娘的遗像,扑通一声跪在贡桌前,泪流满面。“爹娘,我回来了!你们咋个不等我回来啊!”陈三似乎看到了爹娘充满无限企盼和等待的目光。陈三站起身,打了一个趔趄。兰花一声惊叫,“陈三,你的腿咋啦?”“枪伤”。陈三的回答冷冰冰,硬梆梆的,那声音没有一点温度。陈三的话像寒冬一样冰凉,落到地上好像瞬间就会结一层厚厚的冰。兰花端着煤油灯,低下头,掀起陈三的裤管。一个椭园形的,黑色的,鸡蛋大小的伤疤深深地镶嵌在陈三的右腿上。兰花的眼泪簌簌地滚落在陈三的枪伤上,陈三感到一股暖流流遍了全身,僵硬的身体舒泰了,每一根毛细血管都打开到了极限。陈三把头埋在兰花温暖起伏而富有弹性的怀里,温馨而自豪,内疚而自责。兰花说,家里遭遇了火灾,爹娘烧得面目全非,黑二一直来照顾爹娘。爹娘躺在床上,念着你的名字,一直念到咽下最后一口气。爹娘说,看来陈三不可能回来了,黑二这个人老实、本分,可靠,你和黑二不如……兰花低下头,像是做了一件永远不可饶恕自己的亏心事。
陈三拄着拐杖摇摇晃晃地走到门口,拉开门,迈出门槛。陈三大声地喊,黑二,你回来。黑二,你回来啊,我他妈的不是人啊!风雪狂舞,天地黯然,混沌一片。陈三站在门前,任凭风吹雪打,像一棵盘根错节的古树傲然屹立在风雪中丝毫不动摇。冬天的雪拉长了陈三的记忆,冬天的雪令陈三回到了十年前那刻骨铭心而不堪回首的一幕。
雪夜和陈三的命运紧密相连,息息相关。陈三每逢下雪就触景生情,肝肠寸断。雪像一把无形的锥子深深的扎在陈三的心窝里,一扎就是十年。
强劲的风穿过黑夜碰撞着门。陈三那玩意儿瞬间犹如手中握住腰的死蛇,低垂疲软。陈三从兰花身上滑落下来,愈合的伤口隐隐作疼起来,一直疼到心上,揪心扯肺的那种疼痛。“黑二,回来。黑二……”睡梦中,兰花低声絮语,缠绵而心碎地呼唤着黑二的名字。陈三用手轻轻地搓揉着腿上的枪伤,一声粗壮绵长的长叹洞穿了冰凉而粘稠的黑夜。
陈三趁着夜色,拄着拐杖朝队长家走去。陈三不去不行,陈三面临着吃饭、穿衣等现实问题。陈三知晓自己浑身有使不完的牛劲,这身牛劲是在战场上出生入死,摸爬滚打练就的。但陈三知道自己的致命不足和天大缺陷――枪伤。陈三眼里浮现出自己从死人堆里血淋淋地爬出来,双手拄着枪站起来,像一尊巍峨雄伟的雕像顶天立地。连长拍着陈三的肩膀竖起了大拇指。于是,陈三感到了前所未有的自豪和骄傲,为自己的枪伤。如今,陈三要去找队长,这对自己神圣而引以为自豪的枪伤简直就是一种天大的屈辱和践踏。陈三用手摸了一下枪伤,一肚子的委屈和百无聊赖的样子。
陈三走进队长家,队长正靠着门,翘着二郎腿,吧嗒吧嗒地吸着叶子烟,烟雾缓缓升腾,脸上透露出一种威严和傲慢。陈三把右脚的裤管卷得老高,右手按着枪伤的上面,目光在队长和枪伤之间游走。队长说,你有啥事?陈三吞吞吐吐,语无伦次地说,队长,我,你看我这……队长站起来,把陈三从头到脚,从脚到头进行了全方位的扫描。队长的眼珠子在陈三的军大衣上滚动、燃烧,像两颗快速旋转的子弹。队长见陈三没有丝毫反映,皱起眉头说,男人干重活,吃十分工分。女人干轻活,吃八分工分。老弱病残,放马养牛赶羊抓粪,吃五分工分。你这腿啊……队长话没说完,又把目光落到了陈三的军大衣上。陈三的眼珠子像钢蛋一样在斜坡上滚动。陈三弯下腰,把卷起的裤管轻轻放下,遮住冷得发紫的枪伤。陈三眼睛一亮,连忙说,队长,你看我这记性,跳个坎就忘了。陈三脱下军大衣,塞给队长说,回来没带啥,特意给你带了件军大衣。队长摆摆手,丧着脸把军大衣推回陈三手里说,不行不行,你留着放马穿吧。这既是一种暗示,又是陈三急切等待的结果。陈三心里一阵狂喜,满脸堆笑地说,俺媳妇经常说,你经常关照俺爹娘,队长你不收下俺心里不安啊。俺爹娘在梦中一次又一次叮嘱,千万别忘了队长你的大恩大德呀。队长,你若不嫌弃就收下这件破军装吧。陈三说得很动情,也很诚恳。
陈三骑着马,裤管卷得老高,扛着拐杖,一副威风凛凛的样子。陈三骑着马在挑着大粪,扛着锄头,背着背篓的人群里穿行,于是便有了一种居高临下的感觉。陈三用手抚摸着自己的大腿,抚摸着大腿上引以为豪的枪伤,想引起人们的关注和仰慕。枪伤是陈三炫耀的资本。陈三想起了连长一手扶着他,一手把他的裤管庄严地卷起,展示在领奖台上,台下掌声如潮。没有哪个看骑在马上的陈三,更没有哪个把目光落在陈三用手抚摸的枪伤上,陈三感到无比的悲凉。陈三不经意的回过头,看到放下担子在路边歇气的人对着自己的背影指手划脚。陈三的心里便燃起了无名的怒火。陈三首先想到的是黑二。要不是黑二,别人有什么指点的理由和把柄。陈三每晚的怒火在反反复复的燃烧和冷却之间起伏跌落:被子上渗透出恶心的气息,床单上模糊的痕迹,兰花在睡梦中一次次呼唤黑二缠绵的声音。妈的,老子在战场上出生入死,从死人堆里爬出来拿着全家照在沉寂而阴森的大山上疯狂地大笑,想不到盼来的却是这样的结果。狗日的黑二。
岑寂空旷的大山上,陈三的歌声粗旷、雄浑、响亮,像群山一样连绵起伏,像雄鹰一样盘旋,像惊雷一样贯耳。啃草的马群抬起头,用惊奇的眼神望着陈三,像似在捉摸着主人变化无常的微妙心情。夕阳染红了雄壮的大山,骑在马上的陈三把手中的拐杖舞得呼啦啦直响,一副凯旋归来的得意模样。
陈三起了个大早,往怀里塞了两个面蒿粑粑,拄着拐杖一拐一瘸地朝城里走去。爬过了一座座高山,越过了一座座险岭,趟过了一条条深深浅浅,宽宽窄窄的沟道。遍山芳香四溢的野花令陈三陶醉。鸟儿的欢唱让陈三热血沸腾。山尖托住轻柔飘荡的白云,陈三眼睛微闭,自己便舒适地躺在白云里美滋滋地腾云驾雾,神仙般快乐逍遥。陈三从未感受到自己的腿脚是那样的矫健轻盈。
陈三找到武装部,很激动地向一名干部模样的人详细地说了自己的情况和要求。陈三说着便卷起裤管,露出了自己的枪伤。那个干部模样的人没有看陈三的枪伤,告诉陈三这种情况要找民政局解决。陈三赶到民政局时,已经到了下班时间。饥饿像寒风一样一阵阵袭来,穿透了陈三的胸膛,一种对食物的无限欲望令陈三的肚子翻腾涌动。毕竟走了几十里的山路啊!陈三蹲在墙角,从怀里拿出面蒿粑粑,狼吞虎咽,一口气吃了两个个面蒿粑粑,噎得眼睛翻白,脖子僵直,头像爬在地上讨钱的乞丐向来往的路人点头乞怜。陈三盯着枪伤,一张一合的嘴巴像似在对自己的枪伤说着什么。将近下午三点多钟,陈三看到一个年青人骑着一辆破自行车哐啷哐啷急匆匆地冲进民政局的大院,把车一丢,咚咚咚地上了二楼。陈三站起身,一拐一瘸地爬到了二楼。陈三走进民政局的办公室,年青人问,老人家,你有啥事?陈三急切而激动地说,我是国民党兵,安恩溥是我的首长,我打过台儿庄,回来近二十年了,听说可以办理抚血伤残补助。年青人说,有这回事,拿你的证件来我瞧瞧。陈三心里一愣,证件?年青人用疑惑的目光看着陈三,说,老人家,你没有证件?陈三说,证件在战场上丢了。年青人说,没有证件无依无据啊。陈三说,我有证明。年青人说,什么证明?陈三露出了大腿上的枪伤,说,这就是证明。年青人哈哈大笑,眼睛里笑出了眼泪。
陈三走出民政局,恶狠狠地骂了一句,妈的,保住命就算不错了,枪伤也不能作为证据。自己不可以证明自己,日怪的生疼!
陈三接连地跑了几趟民政局,依旧没有个结果。
电影放的是《血战台儿庄》。战场上硝烟弥漫,横尸遍野,血流成河,惨不忍睹。枪声刚停,看电影的人躁动了起来。“打得正起劲,停下来整啥子名堂。”“日本人的坦克好日怪,还会爬山。”“你看那个当兵的,伤成这样违反了点纪律却被杀了。”“把奖赏的银子撒得遍山都是,扛着枪又打起来了。”陈三的全身在颤抖,牙齿咬得脆响,右手紧紧地按住大腿上的枪伤,似乎奇痛无比。陈三闭上双眼,头重重地垂了下去。陈三忽然睁看眼睛,猛然抬起头一声大吼,小日本我日你姥姥,我跟你们拼了。陈三手中的拐杖快速地旋转着,像孙大圣的金骨棒,打在了银幕的“坦克”上。硝烟弥漫的高山上,“鲜血”在白色方正的银幕上荡漾起伏。放电影的大声吼起来,疯子!简直是疯子!
陈三没有看完电影,独自一个人走在深遂浓稠的黑夜里。陈三边走边哭,边哭边喊:“连长,兄弟们全死光了。”“小李子,你鲜血淋淋的双手拿着全家照,好惨啊!”“大牛哥,你的头呢。狗日的小日本呀!”……一阵紧似一阵的枪声穿过茫茫黑夜,击碎了陈三的五脏六腑。陈三抹了一把眼泪,用湿漉漉的手抚摸着大腿上的枪伤,一遍又一遍。陈三抬头一声长叹,声音穿透了漫无边际的黑夜。
陈三回到家,从柜子里拿出一沓纸钱,拄着拐杖来到十字路口。陈三把纸钱在枪伤上来回地拍了几下,划燃一根火柴。火光照亮了陈三扭曲变形的脸。纸钱灰在十字路的上空飘荡、回旋、散落,像一个个游荡的灵魂。陈三抬起头,轻轻地叹了一口气。“杀!杀!杀……”陈三的喊声惊醒了老伴兰花。兰花的眼里闪现出陈三插在桌子上放射出冷冷光芒的匕首。兰花吓得全身发抖,推了推身边睡得鼾声如雷的陈三。陈三一翻身坐起来问兰花,咋啦?兰花声音颤抖地说,别,别那样,都过去的事情了。陈三又叹了一口气说,我梦见连长,小李子和大牛哥了,满身是血啊,好惨!兰花松了一口气,说,别想那么多,睡吧。陈三抚摸着自己的枪伤辗转难眠。
自从看了那场《血战台儿庄》之后,陈三在每年的4月6日这天出现了异常的反映。一起床就把裤管卷得老高,人靠着门,眼睛盯着大腿上黑干憔悴,像靶心一样的枪伤发呆。陈三从怀里拿出一块裹得严严实实的小手帕,轻轻打开,然后拿出那张在战场上视为宝贝而发黄褪色的全家照,紧紧地按在枪伤上,像往风湿关节炎上帖一张镇疼虎骨膏。陈三按住枪伤的手在不停地颤抖,好像枪伤复发,疼得难以忍受。天一黑,陈三抱着纸钱来到十字路口,边点燃纸钱边小声地喊着,连长,小李子,大牛哥……我给你们送钱来了。连长,小李子,大牛哥,昨晚我又梦到了你们,面带微笑朝我走来。连长,今天是你们的忌日,我记得清清楚楚的啊。陈三的声音有点哽咽,颤抖中夹杂着小声的抽泣,分明是在哭。村子边站了一群人,但隔得很远,有的人小声地议论着,疯子,简直是疯子。几个孩子撒腿就想往十字路口跑,被大人一把抓住,屁股上挨了重重的几巴掌。大人们骂道,死娃娃些,想找死啊,他是疯子。
村支书把奥拓车停在陈三家门前,高声武气地喊道,陈三,陈三,天大的喜事啊!陈三拄着拐杖,在兰花的搀扶下步履蹒跚地走出门,张着落光了牙一点也不关风的嘴巴问,要钻土的人了,有啥子喜事啊。陈三和兰花满眼的迷茫,一脸的困惑。村支书连忙说,今天民政局通知,说查到了你当兵的档案,叫你到民政局领钱,好几万呢!你说这是不是喜事啊!陈三抬头望望天空,摇摇头,叹了一口气,什么也没说便转身进了屋子。村支书挺着个滚圆的大油肚,抓了抓稀稀疏疏的头发,又喊了一声,陈三,快上车,我送你去民政局。陈三坐下后,卷起裤管,用形如干柴的双手一遍又一遍地抚摸着自己大腿上的枪伤。村支书急了,大声地吼道,陈三,你老者穷得只有两颗猫都不闻的瘪卵子吊在面前,还死要面子活受罪。陈三一下跳起来,青筋暴露,一声大吼,泥巴都埋到老子的脖子了,把钱带到土里去见鬼。村支书一声冷笑,笑声中带着极大的嘲讽:“你被救济粮胀昏了头脑!”
陈三是在一个大雪狂舞的深夜走的。听到风雪把整个世界搅得沸沸扬扬,陈三依偎在兰花怀里,喃喃细语地说,兰花,我这一生紧紧地和雪捆绑在一起,这是命啊!兰花,我,我对不起黑二……
村公所受民政局的委托,抬着一个大花圈,拉着一块石碑,后面跟了几十个哭丧队的人,朝陈三家浩浩荡荡奔来。石碑上刻着两行字:驰骋疆场九死一生,淡名薄利堪称楷模。那两行字感人肺腑,气势磅礴,横贯长空。哭丧队还没进村子就爹呀娘呀地哭起来,直哭得肝肠寸断,天地黯然,河流呜咽,众人抹泪。
陈三走后,兰花在每年的4月6日这一天便抱了一大捆纸钱来到十字路口,这是陈三咽下最后一口气的夙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