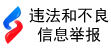二爷的幸福生活(短篇小说)
来源:昭阳信息网 更新时间:2007-11-20 11:52 作者:任天能 责任编辑:
二爷用锯、斧、刨等工具轮番把一块象形木头加以塑造,一块粗糙而简单的木料就变成细腻而骠悍的“卧勾”形犁身;在犁身上端加一截倔强的弯木,弯木变成了倔强的犁把,犁把上再穿五寸园木,二爷的左右手均可轮回把持。在犁身的前端穿一架现代女式皮鞋尖造型的钢制犁铧,称之为犁头。一架堂堂正正的犁就算做成了。望着这架骠悍的犁,二爷就会想象威武指挥牛犁田犁地的情景,这时,二爷脸上的阳光就明媚起来。
二爷用自己亲手做的犁犁地,右手握住犁把,左手捏着皮鞭,眼望天边,大脑里净是在远方打工的娃儿们。女儿随时打电话来要自己不要犁田耕地了,少苦些。女儿还不谙世事的说,犁田耙地赚不了钱,又很苦,苦人不经老,人老了要学会享福。二爷却在自言自语,地地道道的农民,竟然说出这样的话!她就不知道她是为什么出门的。女儿是为了一双火箭皮鞋而去打工的。在女儿心里,穿上火箭皮鞋,就变成了城里人。想到这儿,二爷还想起了那个小伙子和女儿的那件事。那件事让女儿伤透了心。二爷知道,女儿对这个弥漫着牛屎味的家,已经不感兴趣了。她要到城里,把自己变成做梦都在想的城里人。
有一种皮鞋跟木犁穿上犁铧相似,人们都称这种皮鞋叫火箭皮鞋,而没有叫犁铧皮鞋。二爷知道犁铧是专门钻进泥土的,很土气,不现代,不洋派。皮鞋用火箭的象形来命名,既神秘,还含科技韵味。所以女儿拼命的想要一双火箭皮鞋,现在终于穿上了跟犁铧相似的火箭皮鞋。女儿从小穿都是她妈做的布鞋,一直穿到十六岁。有一天,女儿就突然不读高中了。女儿对二爷说,读书有什么用?就算考取大学,大学毕业了,也照样找不到工作,农民依然是农民。于是,女儿便九头牛都拉不回的去了湖南打工了。
事实上,二爷也希望女儿能穿上这种皮鞋,穿这种皮鞋倒是好看了,似乎是城里人了。可女儿是地地道道的乡下人,怎么也不可能变成城里人。可后来女儿还是穿上了。今年女娃子回来过春节时穿上了着一双尖尖的女式红色皮筒鞋的,女娃子想要的东西总算挣到了。但二爷横看竖看,女儿还是不像城里那些女孩子。女娃子还给二爷带了一双白色旅游鞋。二爷说,在农村怎么穿得出像雪一样白的鞋,出门都是灰进屋还要拉牛饮水、喂牛料煮猪食,到处都尘土飞扬的,更何况我天天要跟地打交道,跟田打交道,穿不上一分钟就全部是灰呀、泥浆呀的脏东西了。无论怎样劝说,二爷都不要。最后,女儿哭着说,总不能拿去扔了吧,那你留着走亲串戚时穿不好吗。女儿哭了起来,二爷才勉强收下了白色旅游鞋。
现在二爷看到的女式皮鞋,造型跟二爷的犁的犁身以及犁铧更是接近,但犁铧由于常常与泥土厮磨而光洁发亮,女式皮鞋却因鞋油的修饰以及蹲在酒店里叫喊擦皮鞋的小孩的打磨而熠熠生辉。这种皮鞋反射出的光不能叫亮,而只能称靓,或叫“酷”。擦皮鞋的小孩听说“酷”,立即就抬起头睁大眼睛望着翘着二郎腿眯上眼悠然自得的男主人或者女主人,小孩说,我不哭。小孩以为离开父母时间长了,别人要说他会哭,要说他应该与父母相依为命,与田地长相厮守。小孩是二爷的小孩,是二爷的儿子。二爷的儿子九岁就没读书了。老师对二爷说,你家这个娃娃是跟谁学的?才九岁就会耍流氓动作了,我实在无法管教。老师还说,管你家这一个都管不好,我还要不要管其他的?你还是带回家去好好管教吧。
二爷在老师面前丢尽了老脸,说了很多好话,老师还是不答应。二爷听说学校搞什么三制改革,学生成绩不好老师的工资就受影响。二爷没有办法只有把儿子带回家来跟二爷学犁田耙地去。二爷后来才听别家的孩子说,老师骂二爷的儿子是脓包草包还外加塑料包包。儿子不是会耍流氓,而是学习太差了,严重影响了老师的收入。
二爷的儿子在城里先跟着学修车,学了半个月后师傅嫌他力气小扳不动大螺丝,要他小狗日的滚蛋。儿子后来又去跟着洗车,洗了一个月后老板说他太矮了够不着洗车顶,要他再吃两年的干包谷饭再来。儿子就只有整天提着个提篮到处跑,嘴里喊着“老板,擦皮鞋;老板,擦皮鞋。”儿子只要望着尖尖的皮鞋,便会想到二爷犁田的犁铧。这种类比本来就有点风马牛不相及:犁的光洁与亮度是泥土给予的,犁铧是犁进大地心里的;而“酷”的皮鞋是被儿子擦亮、被天空擦亮,在水泥地皮上笃笃有声。能跟犁类比的,也有,二爷知道就是自己做的耙。
耙是用两匹木质坚硬又有韧性的木料平行固定而成,做法跟做一扇门的框儿一样,只是耙的其中一匹木料的榫头是活动的,可让这匹木方正反翻动。二爷做一架耙是那样的困难,在可翻动的这匹方上打好上大下小的眼子,把烧红的耙齿立即穿进去,然后用斧头敲击,使之边烙边进入;然后用潮湿的酸性泥沙涂抹耙齿和木方,使耙齿边冷却边吸收。泥沙得到铁的耙齿用温度扶贫,根据热胀冷缩的原理,物质胀缩的程度又不尽相同,耙齿就与木方紧密结合,相辅相成,长相厮守;与泥沙相依为命,相互支撑,相互信赖。于是,犁的整体就牢固无比,除非烧烂木方,否则耙齿就无法退出。既然这耙的一方是活动的,那整架耙的稳定结构就只有靠另一边的木方来完成,这匹方就是这架耙的顶梁柱,跟这耙的主人二爷在家的作用极其相似。想到能精心制作出这么尖端的耙,而且二爷还成了这耙的主人,二爷确实是很自豪的。这犁和耙的主人是二爷,这犁和耙的孩子会在城市里擦皮鞋、跟修车师傅打过下手。跟修车师傅打过下手的儿子以后定要具有这耙上顶梁柱的一匹方的作用。二爷这样想。可算路不依算路来,儿子不想成为顶梁柱,也不想跟二爷学犁田耙地,儿子擦皮鞋擦了两年,就是十五岁了。十五岁的儿子也跟着去了浙江,而且现在也跟女儿扭成一根绳,要自己把犁和耙都卖了,把牛也卖了,学会过点清闲日子。可二爷对儿子说,卖了我用什么犁地?用什么耙田?我要拉东西用什么去拉?儿子在电话里夹杂着浙江口音说,你犁田耙地干吗,不就是挣点钱么,你要钱,我寄来给你不就行啦?二爷知道他们姐弟俩是挣了点钱,可挣得也不多,而且还要存下点钱为他们自己的事打个急,二爷不忍心用他们的钱。再说了,二爷怎么可能就闲下来呢,二爷依靠自己的牛,用犁和耙帮别人犁田耙地,换点吃盐点油是没问题的。在农村生活,只要不被饿着,还求什么呢?更何况,二爷跟土地打了大半辈子交道,靠的都是犁、耙和牛,与牛、犁和耙都相厮守了大半辈子,厮守出了感情,二爷怎么离得开它们呢?
儿子和女儿还是经常寄钱回来,寄回钱来二爷还是舍不得卖他亲手做的犁和耙,二爷依然在每一个季节享受着扶犁站耙的快乐,把牛拉在青青草场上,放牧着二爷一辈子对牛的爱情。
女儿和儿子没有办法说服二爷,但女儿和儿子知道如果把牛卖了,二爷需要拉点什么东西就不方便了。于是女儿和儿子为了解决二爷拉东西的问题就想出了一个绝妙办法。但这个办法需要儿子和女儿回来后才能实现。目前只能通过信号在女儿和儿子之间传递,二爷什么也不知道。二爷照样吆喝着牛,把做好的犁和耙沐浴在风中、雨里。
二爷把犁和耙扛去放在一辆手推车上,把装满玉米壳的蛇皮口袋拽上手推车,牛的生活就有保障了。二爷一边去拉牛,嘴里一边喊媳妇,快点给我把车的驾辕抬起来,我拉牛来驾上。二爷媳妇正在加炭煮猪食,嘴里说着来了来了。二爷媳妇甩了两下手上的水,又在衣襟下摆抹了两下,快步走出门来抬起车驾辕。一切就绪,二爷就去找围裙和鞭子。二爷一边走,一边吐点口水裹着刀丝烟,用半截在水里泡过的葵花秆去火炉里点火,火炉上是顿上猪食锅的,二爷把猪食锅抬下来,漫不经心地把烟点燃。媳妇说,你快点去吧,磨光阴不是?
在乡村通往田野的路上,一头牛拉着一辆车,二爷的屁股坐在犁的“卧钩”中间,那“卧勾”就很踏实;二爷脚踩在耙齿的缝隙间,这习惯性动作成了耙的依恋;二爷的背靠着蛇皮口袋,蛇皮口袋里面的玉米壳就没有了孤独。从二爷嘴里、鼻孔里冒出的烟雾,尾随着二爷晃动的牛车,飘散在路的尽头,一幅生机昂然的启程油画时不时就拓印在儿子的大脑里。
二爷在田里犁田,左手扶着犁把,走两步又往右边用力扳一下,右手握着鞭子,不时撩一下,嘴里唱歌似的吆喝着:“哩哩――咐咐”。
牛听二爷一辈子的话,听懂的人话就是这一句“哩哩――咐咐”。“哩哩”是向左转或是朝左边一点,“咐咐”是向右转或者靠朝右边一点。牛要听懂二爷这句话也不容易,就像中国人学英语,一个单词要根据具体语境来判断才知道它的真正含义,有过去时,现在时,还有将来时。牛要判断“哩哩”是向左转还是靠朝左边一点,就要看在哪里在做什么了。如果是遇到了岔路,就要牛选择左边那一条;如果单独在路上走或者拉着牛车走,就是要牛靠朝左边点让后面的车;如果是在犁田,靠朝右边了犁着田的面积就小,就是牛在偷懒、不使劲,所以二爷要牛歪朝左边一点,不要偷懒,二爷嘴里就要歌唱着“哩哩”。牛和二爷关系好,二爷是舍不得用鞭子抽打牛的,二爷只要嘴里歌唱“哩哩”,牛似乎像人一样就心领神会了。二爷知道他喂养的牛是通人性的,牛贵有自知之明的。牛真的通人性,不会因为二爷吆喝了“哩哩”而假装没听见。二爷的牛是很乖巧的,牛拉着犁使劲地犁起一块块泥土,被二爷握着犁轻轻一翻,泥块就乖乖靠朝一边,看上去光溜水滑、平整发亮的。二爷也希望女儿和儿子像牛一样的听话,希望女儿和儿子也像这被犁过来的泥土一样光溜水滑、平整发亮就好了。可他们却离开了二爷,这都不说,他们还要二爷卖掉犁和耙了,把牛也卖了,这怎么行。
牛累了,二爷的全身也都冒汗了。这时,牛站在田里吃玉米壳,二爷蹲在田埂上裹着刀丝烟。二爷的烟雾,要么缭绕升上天空,要么随风而去。
有水滋润软了的田,好犁,二爷一个人就可以摆平了。要是泥土硬度大,牛就很吃力,二爷就很吃力。二爷吃力的时候,二爷就想儿子,以前儿子是整天提着一把壶或者胶桶,随时跟着二爷走,跟着牛走,跟着犁走。牛和二爷都很吃力的时候,儿子就浇些水在犁铧上和泥土上,充当润滑剂,泥土就要倒得快一些。儿子一边浇水,一边能捡到一些玉米颗粒大小的茨菰、荸荠。儿子心里非常高兴,带着回家去就跟周围的小朋友分享。但二爷对儿子捡茨菰和荸荠就非常不高兴,二爷要儿子捡牙齿草的根,二爷说那东西到第二年就会翻倍的疯长。二爷说,牙齿草一疯长,稻谷的营养就被牙齿草给吃了。儿子就只有极不情愿地一边浇水,一边捡牙齿草的根,捡了装在裤包里。晚风不住地刮来时,二爷的全身直冒汗,牛身上的汗却被风干了,儿子的裤包里也装满了牙齿草。这时候的二爷就很高兴,回家后就把影响稻谷生长的牙齿草洗干净拿来炸了下酒。
凡属犁过的田或者地,都必须经过耙的加工方可进行栽种。这样,犁和耙就常相厮守,就相依为命。二爷耙田的姿势是让人陶醉的,他站于耙上让牛拉着在水田里前行,就像北方人滑雪橇那样潇洒悠闲。只是二爷的手要掌握牛的方向,嘴里吆喝“哩哩――咐咐”的对牛的口令。二爷侧着身子,让脚一前一后,脚还要使暗力对耙掌握个平仄,适当时用脚把能转动的那匹方翻过来,让尖尖的耙齿迎着自己光光的脚。儿子以前看到这些情景,就编成故事去跟其他人讲电影电视里那些上刀山的情景。
黄昏来临时,二爷收工了。这时的二爷就舍不得坐上车让牛拉着,而是自己走路。走着走着,二爷就想起了从前是让小孩来拉着牛走的。不然牛就会因为饥饿而掠一口路边的庄稼。二爷想,儿子现在在浙江,要是没有生意、找不到吃的会不会像牛一样掠一口路边的庄稼呢?
二爷回到家里,牛还没有卸、犁和耙还来不及下车,二爷就倒在了床上呼呼大睡。二爷的媳妇又得去做二爷剩下的事情。
二爷进入梦乡的时候,远在浙江的儿子也同时做了梦,只是二爷的梦境和儿子的梦境没有交叉部分,儿子常常在梦里飞了起来。二爷的梦与犁、耙和牛常相厮守。特别是牛,牛是二爷的命根子。二爷没有耕地犁田的时候,二爷就放牛。二爷保护自己的牛,就像保护生命一样。二爷知道牛在一家人的生活中,一分一厘都得从牛身上要,所吃的每一粒粮食,都是二爷和牛辛苦得来的。假如没有二爷,也不知一家人会怎么过;要是没有牛,二爷一家人就无法过了。二爷在放牛或者用牛时,都时常不离牛的身边,生怕牛被别人偷走。二爷怕别人趁自己的牛在吃草、没有人在身边,就在牛身上轻轻的锥一针,等过了一个半个时辰,牛就慢慢梭脚了;或者有人在牛草上放点毒药,要么把药放在其它食物上给牛吃,等到太阳落山后,牛开始归家,就死在了回家的路上或者死在牛厩里。那时,你说是谁放的毒也没有根据,死牛摆在你家门前,要卖你就卖,不卖人家也不勉强。到时候你还得去求别人来买,更是叫你哭笑不得,痛不欲生。这是村子里已经发生过的事情,二爷得警惕才是。二爷随时提心吊胆,牛就是二爷的一件衣裳,二爷随时都把它穿在身上。就算二爷跑到沟沟坎坎撒泡尿,眼睛也是盯着牛的。就算是背着牛撒尿,二爷的头都是转过来望着牛的周围的。如果牛会讲话,牛肯定会说你安安心心撒你的尿,你回过头来望着我你不害羞吗。二爷要在野外解个大溲,都要前后左右观看,估计没有人在他解完大溲时跑得到牛身边,二爷才敢蹲下去方便。
二爷是这样的爱惜牛、保护牛,二爷也觉得似乎有些过分,事实上,二爷为了亲爱的牛,为了保护心肝宝贝的牛却伤害了女儿的心。女儿出去打工,除了女儿冲着那双犁铧似的火箭皮鞋出走,更大程度上是跟二爷和二爷的牛有关。
为了安全起见,二爷不敢把牛关在外面,而是关在家里,人睡楼上,牛睡楼下,楼下分成两截,前面是“客厅”加“厨房”,后半截就是两个房间,一边要宽一些。是自从二爷结婚做新房后就是二爷和媳妇的专用房间了;另一间要窄一些,让儿子卡在里面将就着睡。有了牛后,二爷就把专用房让给了牛,让牛跟自己生活在一起。牛厩里粪水多了,二爷去舀掉,垫圈的草没了,二爷去加上。儿子的意见是挺大的,但再大,儿子又敢怎样呢,不关在屋里二爷放心吗?
早晨牛出去要经过“客厅”,二爷就把锅锅家什拉开,让出一条牛路;晚上幕归回来,把牛喂饱喝足,又得把火塘边放着的东西拾出一条道来,牛才进得去。而且,每晚二爷要睡觉,除了锁上门销,用铁柱去把门销扣紧,从外面用刀子拨不开门销;二爷还用一把锁去锁着,最后再用扁担去抵住门销。深夜了,二爷把这些都做好后,还要去看看牛是否安然无恙,再回过头望上几眼门,才上楼去睡觉。
二爷觉得这样倒是安全了,可就不卫生了。虽然来自己家的大都是农村人,但实在窝囊很了也会让人瞧不起。牛在下面,人睡在上面,二爷时常会嗅到一股牛粪味,熏去熏来,二爷都感到恶心。但是,二爷劳动一天回来,都很疲倦了,吃完晚饭到深夜睡去,一上铺就“南斯拉夫”,那牛粪味儿的感觉就不那么明显。
牛关在家里时间一长,自然就会有些粪水,粪水一多,又会往外沁。所谓外,是牛厩的外,其实就是堂屋中。有些时候一家人正在吃饭,那一股粪水味儿就弥漫开来,叫人难以咽下饭去。二爷倒不警觉,只是女儿和儿子每到吃饭的时候就夹几筷菜在碗里往外跑。有客人到水生家来,水二爷媳妇有些不好意思。媳妇无可奈何地对二爷说,你要想想办法了,有个人来实在不雅观。二爷低着头不言语。
一天中午,邻村小张来请二爷犁田。小张其实不完全是为田的事而来,小张是冲着女儿来的。小张早就看上了女儿,而且和女儿早就有来往。只是女儿还没跟二爷说过这件事情。那天小张来,想给二爷一家有个好印象。出乎意料的是,小张一进屋,就嗅到一股草料味。小张一看,房门边沁出了橙黄色的水。小张就和女儿到门前的樱桃树脚下乘凉。快要吃早饭了,二爷扛着耙,吆着牛就回来了。小张忙对二爷说,来我帮你。小张就去替二爷帮着把耙卸了下来。二爷很累了,就进屋去坐在草墩上休息。小张帮着二爷送牛去饮了水,回来后就一直吆到牛厩里去。女儿已把饭菜做好,端出来放在桌子上。小张朝桌子边经过,嗅到的是饭菜的香味和牛身上的一股草味的混合味道。这都不说,牛身子刚进牛厩门的一半,牛就吧嗒吧嗒的拉起了大便。这就不妙了,房门前有一张桌子,桌子上放着砧板,砧板上面有一大碗女儿刚刚切好的肉,那稀牛粪吧嗒吧嗒落在地上后又溅起一些来,砧板上的很明显,碗里似乎也有,小张就不好多看了。这牛拉粪也不争气,早不拉,晚不拉,偏偏在有客人的时候出了洋相。
女儿走到桌子边,装着取走砧板,就把碗里不该让人看到的一点肉拈走。这,小张是看在眼里的了。
快要吃饭了,小张突然喊肚子疼。二爷忙跑到背后菜地里去找苦生根,二爷说用红糖兑苦生根能治肚子疼。小张对二爷说,不用了,以前我的肚子就疼过,我爹托人到山里去找了一种药,我要吃那种药才起效。小张搂着肚子一边说,一副愁眉苦脸的样子。二爷赶忙叫女儿送小张回去。到了中午,女儿回来了。女儿是哭着回来的。后来女儿就哭着离开了家乡,到了遥远的湖南。
小张不跟女儿好了,女儿现在肯定怨恨二爷,但毕竟是父女,女儿还是寄钱来,还在想着让二爷把犁和耙卖了,把牛卖了的。至于儿子,儿子在家里跟牛睡在一起,也是嗅够了的。儿子和女儿是坚决要让二爷过上幸福生活的,而目前阻挡二爷过上幸福生活的,就是二爷的牛,二爷的犁和耙。儿子和女儿商量,一定要把挡住二爷幸福生活的东西搬掉。
转眼间又要过年了。儿子和女儿都跟二爷说过已经分别从湖南和浙江车站出发了的。但二爷掐着手指头算,不论如何耽搁,今天也该到家了。可就是没有到。
儿子和女儿到家的时候,出乎二爷的预料。二爷看着儿子是开着一辆三轮摩托车来的,女儿坐在车后,儿子突突突的就把摩托停在了家门口。姐弟俩当初是想来个突然,让二爷惊喜。可二爷看见是一辆新车,知道是小子出的馊主意,二爷脸上就乌云密布。要是在以前,对待不听话的儿子,二爷通常是雷雨交加,儿子的屁股上有闪电般划破的横七竖八的红印,可现在儿子毕竟大了,况且,姐弟俩刚从远方回来,再打骂儿子,就有点不近人情了。但要是家里没有拉东西的还好说,有着牛、还有牛车,这不是浪费吗?这两个糟宝!二爷气得话都说不出来。二爷睡了三天三夜才起来。
过年了,再不和女儿、儿子搭话是不恰当了。正月初一,女儿无事找事的和二爷说话,二爷爱理不理的。女儿说,我想到我舅舅家去。二爷说,你去你的。女儿说,爸爸,你不也多长时间没有和我舅舅在一起了吗?女儿知道二爷只和舅舅谈得来。二爷半推半就的跟着女儿去了亲戚家。
二爷回来的时候,第一眼看到的是,竖在家门口的耙不在了,二爷走进家里一看,牛圈里的牛也不在了,犁和牛车都统统的没了。二爷气得直跺脚。
女儿说,爸,要拉洋芋包谷的用三轮车不也一样的吗。二爷说你两个合起来骗我。女儿说,你一直靠给人家犁田耙地,这样苦也只能换吃盐点油的钱,把它们卖了,零用钱我们也是挣得来的。再说了,要拉东西,我们买三轮车来还不方便吗?
二爷知道女儿说的是道理,但二爷无论如何也接受不了这个现实。二爷知道,自己的根早已深深的埋在了农村的泥土里,就算连根拔起,灵魂也是在土里的。
二爷说,这个小杂种,把老子的命根子都割断了。
二爷到处的找儿子。可儿子知道二爷的脾气的,早就有所准备,提前坐火车走了。
二爷很想打人,但历来都只敢打儿子、不打女儿的,更何况现在都是二十有几了大姑娘了。
女儿走后的第二天,二爷突然的不会讲话了。二爷成了一个哑巴。
哑巴每天在村子中行走,走到有牛的人家门前,去看看犁头、摸摸耙齿,和牛“含情脉脉”一阵。每到一家,有的称哑巴二叔,有的称哑巴二哥,都说你不要看了,不是卖给我家的,是被你儿子卖给了一个外地人了。哑巴只是摇摇头。隔了几天,哑巴又去看了。看上几次,有些人家就有些不耐烦了,不给二爷好嘴脸看。二爷虽然说不出话来,但二爷是有自尊心的,二爷也就不再去了。
后来二爷每天都要到田边站着发呆。望着田里,就眯上了眼睛,鱼尾纹的下面,似乎闪现过一缕淡淡的阳光,阳光慢慢地消失了,二爷就深深地叹气。
有一天,二爷突然栽倒在了一块正要插秧的田里。等人们发现去把二爷扶起来的时候,二爷早已僵硬,身子是佝偻着的,无论如何拉都拉不直,就像他一生割舍不断的犁铧,歪斜着身子,默默地对视着苍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