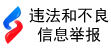到天上寻找水源(短篇小说)
来源:昭阳信息网 更新时间:2007-11-20 11:44 作者:任天能 责任编辑:
1
月亮升起来了,星星一闪一闪眨巴着眼睛,像聪明人在给不聪明的人使眼色、递点子、出馊主意。今晚上大家到广东院的干渠去偷水,就是水生出的馊主意。水生说,天干了就要让老子们饿死不成。走,怕个球。
就在早上,水生还站在自家干脆了的田垡子面前,把锄头重重的笃在田垡子上,右手拄着锄把,锄把被水生的手紧紧捏住,拇指和食指中间的汗水都被灰尘沁黑。水生眼睛直勾勾盯着天上,巴望着天上下雨。可天怎么能按水生的想法说下就下呢?
眼前的干垡子像干脆了的面包,舌头惹不起,牙齿嚼还怕伤着牙龈。水生穿着的是一双剪子口的布鞋,虽然鞋底是汽车轮胎割成的,耐磨且有韧性,但水生还是怕用汽车轮胎去嚼那干脆了的田垡子面包。被干脆了的田垡子,随便一个有棱角的泥土尖尖,都可以把水生的脚杆剐破,至少剐起一条惨白的路。况且,田里没有水,水生下田去也不起任何作用。水生只能干着急。
水生去看过秧田里的秧苗的,秧苗绿油油的,遇到太阳好的日子就拔节生长,老辈人都说秧苗是见风长的。现在秧苗都三寸多深,早就可以移栽了,再不移栽就要长成老憨秧了。要是在以前,秧苗两寸深就可移栽,可现在田里仍是干垡子,这不是要水生的命么。好在水生家的秧田里面是有水的,秧苗才如此茁壮。但那秧田里的水是水生带着媳妇在水井里一挑一挑挑来的。在吊井边,一些婆娘要挑去洗菜做饭洗脸喂猪,媳妇却要挑来救秧苗。为了抢水,媳妇跟个婆娘吵了扭打在一起,媳妇的脸这段时间都还像猴子屁股样有红一条紫一条的纹路。
水生抬起锄头在干垡子上使劲地锤下去,一团灰在空中打个旋儿就被南风掠走。干垡子被水生的锄头抖落几个棱角尖尖,剩下一个白印子,锄背也紧紧沾上田垡子的粉末除去不掉。
水生无可奈何的又到堰沟边去看。水生家田里的水是要从堰沟里放的。堰沟边,刚重新改建成三面光的堰沟坝埂被太阳晒得起了火,坝壁被太阳晒了反射过来一股热流,朝水生迎面扑来,水生感觉脸和袒露着的胸都热辣辣的。沟底的泥浆被晒了裂开大个大个的口子,虫虫蚂蚁在里面翻进翻出。堰沟里死牛烂马被太阳炙烤了生蛆,大概那些虫虫蚂蚁把死牛烂马当成了最好食物。遇到天这样旱,虫虫蚂蚁就行动起来,这是它们出行劳作的好日子。一些光着屁股吊着脓鼻涕的小孩也在裂开的沟底追逐虫子。以前水生要放水泡田,不管天有多旱,只要到这堰沟里来扳开涵洞的石头,水就汩汩顺着小溪欢快而下。不单水生家,松树乡大部份稻田、秧田都用堰沟里的水。自修了利民水库后,成立了水库管理局,水库里的水统一由管理局管理、分配。水库刚建起时,春耕时需要用水,堰沟里就有水,平时不用,堰沟就是干的。可从去年开始,生产用水就需缴纳水费才统一放水了。水生想起一句话:“水是农业的命脉。”现在命脉断了,农业生产也就没指望了。
2
中午,水生只身一人到了主干渠上。水生递一支烟给守涵洞的人点燃。
水生说,没有水是插不上秧苗的。
那人说,是啊,没有水怎么插呢。
水生说,插不上秧又吃啥呢?
那人说,是呀,插不上秧吃啥呢?
水生说,所以农民最要紧的就是水。
那人说,庄稼离开了水就不能活。
水生说,老兄,那就分点水给我去把秧插上吧。
那人说,那你等我们把水放够了你再放吧。我们这么远的跑来你们县放水容易吗。
水生说,我的一小块田就只要点漏沟水就够了。
那人说,你不要看着渠里的水淌的欢,也许我在这里守多少晚上,轮到我家田里连一小股漏沟水都不会有。而且我们这水是出了水费的你不是不知道。
水生说,你意思是我们就没有出水费啦?
那人说,这个就不关我的事了。反正这段时间是我们的放水期,你们轮到什么时候放水上面会安排的嘛。
水生说,你就睁只眼闭只眼,你看我们的秧苗早就长成老憨秧了。再没水就插不上了,插不上又吃啥呢。
那人说,我们那么又远,你们可是近水楼台啊。
水生说,现在是近水楼台不得月了,你不准放,哪来的水呀。
水生觉得这人是不吃软的,得让他吃点硬的。
晚上,水生来到二狗家,水生说,天这样旱,看来是栽不上秧了。
二狗说,这就日怪了,水库里明明有水,却得不到用。
水生说,我们原来那是自己整自己。
二狗说,什么自己整自己?
水生说,你不记得了,那水库是我们跟着去修的。
二狗说,你还说,都是你们做的缺德事。你以为你可以表功了,你跟着修了水库你自己也得不到水用了。怪谁?
水生说,现在不是挖苦的时候了。现在参加修水库的和没有去参加的都一样,都栽不上秧。得想想办法。
二狗说,总不能眼睁睁看着秧苗长成老憨秧吧。你说怎么办我们就跟着你干。
二狗一边说一边看了看灶屋里。灶屋那边媳妇正在做晚饭,大概是没有听见。水生怕二狗媳妇听着,二狗媳妇在家是母老虎。那次二狗被媳妇这个母老虎吓得躲到了桌子脚下,二狗说怕是不怕的,出是不出来的。媳妇手捏一根扫桌子的鸡毛棍,就倒过鸡毛棍,想用没有鸡毛的一头去戳二狗。这时候水生来到了二狗家门口,走进屋里来,水生很尴尬,想悄悄的走了也不恰当。因为被躲在桌子脚的二狗看见水生是站在门口的了。二狗媳妇没有正面看到水生,但二狗媳妇从余光里明显感到有人站在门口,媳妇便慢慢把鸡毛棍转过来,手捏着没有鸡毛的一头,用鸡毛在桌子上去拭灰尘,一边扫一边对二狗说,我说你呀,就是个咬卵匠,我都说两个人抬呢,你硬要一个人背。听这样的话,二狗的脚轻轻一垫,就把桌子背了起来,放在火塘边。水生笑着说,我就说你们家二狗很会体贴人的。看吧。人家多会替婆娘着想。水生进屋来后,二狗一家好像什么事也没有发生过一样。
二狗怕婆娘已经听到自己说要跟水生去,婆娘肯定会阻拦,二狗没有说什么了。水生说我去上个厕所。二狗说,我是听着别人屙屎屁眼痒,走,我也去。出门来,水生说,今晚上我要去偷水,你去不去?二狗说,只许你家栽上秧,要把我家饿死呀。水生说我是怕你媳妇不准你去。二狗说,男子汉大丈夫的,谁怕谁呀。二狗媳妇问,你们要去哪里?二狗说屙屎屙尿,是正大光明的,你管得着吗?二狗一边说着,悄悄的扛起锄头跟着水生走了。
水生带着二狗来到了三娃家。
三娃说,有人瞧涵洞吗?
水生说,水这样紧缺,怎会没人瞧呢?不过你狗日不去算球了?反正到时候水下来你是没资格站在你家田边扒田口子的。
三娃有些犹豫。
水生说,我知道你是缩头乌龟。水生递了个眼色给二狗。水生说,咱们走。
三娃也担心那长得老高的秧苗移栽不上,三娃忙说,主要是怕有派出所的人跟着来干涉,不然怕个球。走嘛。
3
在往广东院去主干渠的这条路,谁都很熟悉的,即使像今晚上这样伸手不见五指,哪里有个坑,哪里有条沟,谁都能如数家珍。特别是水生,路途中哪里有个石头,闭上眼睛伸手去就摸着了。水生是最熟悉不过的了,原来跟着去修水库,水生在这条路上走了多少年。水生脚上走起血泡,在路边找一颗树上的刺来刺破血泡放了血水,又继续前行了。在哪个僻静的地方撒过泡尿,水生记忆犹新;在哪个石包上歇过气,水生记得有个石嘴硌过自己的大腿;通过哪个村子被狗撕破裤子,水生点得出狗的主人的名字。现在,路还是那条路,房子还是那些房子,就是水的流向发生了改变,水原来从山脚流淌,在村子中穿行,给人们洗衣服洗菜,放到稻田去栽秧。人们都说这是鱼米之乡,是山区姑娘向往的除了城里的最好的地方。现在水生家村子中的沟壑是干的,几乎没有流水从沟里经过,水是绕开水生住的这个村子爬上了山腰,在山腰恣意汹涌到别的县去了。
黑夜里,二狗第一个出声,二狗说,干渠的水太大了,要是能够全部放下来,所有的田只要一天就全部泡完了。又有人插话说,只要用几颗雷管,就可达到你说的目的了,那咱们今晚上就不用偷偷摸摸的了。水生听着这人奚落二狗,说二狗天真。意思是只要给放水,用雷管炸开一处,水就可以放下来,还用得着这么多人去偷?水生没有作声,水生在想,不要说用雷管了,今晚也许一滴水也放不下来,而且危险性很大的,来瞧涵洞的人不是涨干饭的,要是打起来怎么办?打伤了谁打死了谁哪个来负责?就算出乎预料的能顺利放点下来,结果还是要被发现的。追究下来,跟着一起去的八个人都是水生去发动了来的,水生就成了教唆犯了。这样想着,水生就有些畏缩。水生祈祷这时候大大的下一场雨,而且下了涨洪水,水生也就不会带着他们去偷水,自然也就没有什么责任,而是各自去放天上下来的雨水了。雨水是免费的,不需要放闸门,不需要缴费,更不用需要偷偷摸摸。雨洒下来后各家堵了就算各家的了。这样想着,水生就觉得主干渠的水也是天上的雨水,是自己跟着去修了水库把雨水聚在一起的。这样一想,水生的胆量就要足一些了。可天上怎么会下雨呢。这些天是不可能下雨的。
按节气每年端阳节都要涨端阳水,还没有栽上秧的人家在那天晚上都要全家老小出动,去收集端阳水。无论怎么说,最迟不超过端阳节都要栽上秧的。可现在端阳节早就过去了,仍没要下雨的气象。而且水生从电视上知道还要干旱一段时间呢。看来对望天水是彻底没有指望的了。
水生说,路上遇到人千万别讲话。特别是二狗,你那张嘴要管得住,我怕你那张×嘴惹祸。
二狗说要是遇到熟人你去搭腔?
水生说,是熟人也不要理他。你知道我们去干什么吗,我们是去做贼。做贼也要让你的熟人知道吗?水生说着就自言自语的骂了起来,水生说,日他妈,原来明明是我们自己用得好好的水,自己去修水库堵断了水,现在要用也得做贼去偷。难道老子们不活了?
二狗说,水生说的对,不能让人知道,如果有人问,大家一起说:去偷你家的。大家一起出声,别人听不出来,反而要被吓着。
水生说,既然来了,就没有回头的路。白白的回去,田里就不可能有水。不来就要趁早,现在来了,就一定要想办法把弄点下来。
水生说,如果他们人多也不准哪个跑,那个跑就是狗日的。这一赌咒,跟喝鸡血酒没什么两样。
大家高一步低一步、悄无声息地在原来去参加利民水库建设的路上走着。
想起修水库来,水生更日气。有一次,水生跟着从山上抬石头下来支砌挡墙,在崎岖的山道上抬石头,一个在上坡,一个在下坡,在下坡的就要吃力一些。水生力气比后面的人大,就在前面开路。水生抬着石头在下坡憋着气慢慢走着,脚底踩着了黄泥巴,黄泥巴是潮湿的,水生站着的脚就往下梭,梭了五寸远就到了悬崖边,悬崖边恰好有一小个石头支撑住了水生的脚,才使水生站稳。过了以后,水生满头大汗,多少天都还会做噩梦。回来母亲听说水生犯危险,就不让水生去了,母亲说,在生产队跟着大家挣多吃多,挣少吃少,反正饿不死。可父亲却说,这是支援社会主义建设,娃儿就是要拿去锻炼,不锻炼怎能成钢?你看咱们没有碳,挖树根都要去挖来炼钢。你看我们的娃儿是没有胆量的吗,被一次就被吓倒了吗?!
父亲不希望水生成为懦夫,水生的父亲就是被野狗拖去,被乡亲们打着火把去追回来的。现在父亲的手臂上都还有野狗的牙齿印。父亲也是死过一回的了,现在父亲照样胆量十足,照样跟着去大挑大挑的挖树桩来给生产队炼钢。想起父亲身上的伤疤,水生就更坚强了。
水生当时是响应号召去参加利民水库建设的。
当时队长说修好了水库,可以为解决农业用水和饮用水。松树乡是从来不缺水的,但饮用水却很困难,春冬两季,水井边就排了长长的等水队伍,随时还为插队发生争吵。水生在城里读书,用的是自来水,回家里后听说修了水库就能用自来水了。水生觉得城里的学生都还要上山下乡,自己不是城市人,还没有资格当知青。现在回家来跟着去参加社会主义建设,不就是名正言顺的知青了吗。其他人是生产队长费了多少口舌才去的,而水生却是自愿参加的。在生产队长开社员大会的表扬中,水生更是热情倍增,水生又亲自去动员了其他的几个大小伙子一起,戴着大红花雄赳赳气昂昂奔赴支援利民水库的前线。生产队长还因民工任务超额被大队表彰。
现在水库建成后,却把日夜奔流的堰沟水堵断了。洗衣服浇菜喂猪洗碗的用水就不方便了,这些困难还可以克服一些,鱼米之乡的田里找不到水,那米从哪里来,鱼在哪儿跳呢?不成鱼米之乡也无所谓,只要能有吃的。问题是现在没有水下田,田里栽不上秧,就意味着谷子颗粒无收。
现在水生感到后悔,当时就不该积极的去修水库。耗子拖秤砣是自塞门路。修水库不也是自塞水路吗。
当然要用水也是可以的。只要交了水费就可以。
现在松树乡的水费还没有上缴,水库管理局就不放水。松树乡组织人收水费,有的人家确实没有钱交,有的人家有了钱也不交,认为自己原来都有水用,现在把自己该用的水堵断了来收自己的钱,理由何在?就是不交。这不是将自己的油炸自己的骨头吗?一些人参加过水库建设,现在还是得交钱,心理就不平衡,也磨蹭着没交。还有一些人懂点政策、法规,知道现在国家非常重视农业,围绕“三农”正在做很多工作,还搞新农村建设呢,原来有水用,现在更重视了反而连栽秧的水都没有了,岂有此理,就是不交。大家都不愿交。有很多人是外出打工的,田地都放了荒着长野草,你去找谁收水费?就算外出打工的也有把田地承包给别人的,但承包时没有谁考虑到交水费的事情,承包者要是交了就亏本,谁愿意呢?
当然也有上交了的,但上交了还是没有水用。因为管理局只认政府,钱交齐就放水,拖欠是不干的。疼脚带牵好脚,去年交了钱的人家没得到水,今年有钱了也不交。乡政府和村两委也无奈。
4
月亮灰蒙蒙的,但水生还是模糊看到了,有一个人用一件军大衣裹着身子蹲坐在一个背风的路坎下,面对着涵洞。
水生快要走到涵洞时,那个人影警觉地动了动。
水生说,喂,给是人。
没有应声。
水生说,你是鬼老子就要用石头砸了。说着水生就弯下腰去假装捡石头。
那人说砸不得,砸不得,我是瞧涵洞的。
水生走近那人,水生瞅了瞅那人说,瞧涵洞那个中午我见过,你到底是干啥的,你是不是来偷水的?
那人说,我真是瞧涵洞的,我俩换班,他瞧白天,我瞧晚上。那人说,夜半三更的你来整啥子?
水生说,去丈母娘家,从沟埂上过。水生说你给有火,烧支烟。晚上摸黑路点上烟就不怕了,鬼是怕火的。水生递上一支烟去。
那人边接烟边说,怕什么?我从来没有见过鬼。
烟火一明一灭,水生看清了确实不是中午那个,话音却是一样的,是外县的。水生说我们这些地方时常会听得到鬼叫的。有火,鬼就不敢靠近了。那人说,不要吓我,我从来都不怕。我只听说鬼怕恶人,还没听说过鬼怕烟火。况且我身上有东西的。水生说看来你身上有佛章。那人说用佛章是骗人的鬼把戏,我从来不相信那一套。一边说,一边轻轻拍了一下放在右手边的地上的东西。
水生说那是什么宝贝?那人说有了这个就不怕邪恶,豺狼虎豹也不怕,走村串户有狗,更没有问题。水生说,你真正看到了是什么,就不会怕了。可要是什么都没有看见,却有一种奇怪的声音围着你叫,你那家什就起不了作用,你就会抖、就害怕了。水生一边说,一边大口把烟火吸了一明一灭的。
水生说,这地方有野猫,野猫的叫声是很真吓人的,你听到过没有?那人说,我不怕。
水生说,那声音从天空突然传来,看又看不见什么,却阴风惨惨的就叫到你身边了。害怕得很的。你听我学着叫两声给你听你就知道了。水生就学着野猫的叫声叫了起来。
平时水生学起来很像野猫的叫声,而今晚喉咙刺疼,发出来的声音更让人害怕,真的有些吓人,没有听见过这种声音的人肯定就要说鬼的叫声就是这样的。水生自己都觉得奇怪,怎么叫出这种难听的声音,这声音好像是一种十分痛苦而又无奈发出的惨叫。
水生说,你听听像从哪个方向发出的声音?那人仰着头转着身子判断。水生一边叫,趁烟火看准了那家什,很快就拿到了手。那人并没有料到自己的家什到了水生的手上。那人说,我没有听着声音像从哪棵树上发出来的,不就是你在叫?那人说我倒是听着下面有一帮人从这儿上来了。
水生说,是的。我也听着了,他们是来放水的。那人问你怎么知道他们是来放水的?水生说我是估计的,稻田里一滴水也没有难道要把老子们放了饿死?那人觉得不对劲,一就去摸自己身边的家什。水生说,不用了,在我这儿呢。那人说你拿我的匕首整啥子?水生说,我看看是什么东西,到时候我会还你的。我不要你的刀,我们只要水。
坡脚的二狗、三娃他们听到水生学野猫叫的暗号就摸上来了,到了瞧水人背后。瞧水人嘴里喊说这是我们的水,我们出了水费的。但瞧水人被三娃紧紧的连手臂箍住,嘴被另外几个用封苹果箱的塑封纸封住了,只有鼻孔能呼吸。几根尼龙绳子从瞧水人肩膀上一直缠到了脚。为了保险,还把脚也捆了连接在一起了。水生说钉一个木桩,把他固定在木桩上,怕狗日的横扳直跳滚下沟去泡死,那就惹祸了。水生对瞧水人,对不起你,我们这是没有办法的办法,我们只放一夜就够了。到时候我们会来解开你的。你就暂时忍受一下吧。
5
主干渠的水泛着微波,在月色映衬下,波光闪闪发亮,大家看到闪闪发亮的水就心动。
水生说,下去一个看看水有多深。水生没想过自己怎么就变成了总指挥的角色了。水生没说要谁下去,反正大家的事大家做,谁下去都行。
没有应声。
过了一会儿,二狗才把锄头往渠坝上一扔,脱了衣裳就纵身跳下去。二狗平时都听水生的话,水生说一他不二,水生虽不是村里的什么,但二狗要盖房子没地基,水生就给二狗出主意;二狗要只要碾好米要上街去卖,水生就说这些天价格起不来你去找宰?二狗就乖乖的蹲在家里。有人说水生出的是馊主意,但二狗却说,馊不馊,只要管用就行。水生说的,二狗一般都会照着去做。
二狗不会游泳,更没学过跳水,但二狗觉得水生兄弟带着大家一起来,自己不跳也得有人跳。二狗双脚一并往下纵的。二狗身体结实,但个矮,水没了他的头顶,二狗在水里扑嗤扑嗤的吐着水,双手扑腾着。水面看似平缓,实则因渠坝三面光,再湍急的水也难涌起波涛。就像看水生平时老实巴交,谁也不会想到他会带人来偷水一样。
二狗的脚踩不到底没支撑,被冲着往下走。水生立即拿起锄头,双手捏住锄头叶子,用锄把去探二狗的手。二狗紧紧揪住锄把,才往渠边游过来。渠坝光溜水滑的,几个人抓住了二狗的手才把他拖上来。二狗被呛了几口水,爬上来说,放它挫球,差点把老子呛掉了。
水生说,人怂了,你看我的。水生连衣服都懒得脱就跳了下去。但水生还是被冲了一段后才立住脚根的。水生比二狗稍高点,水还是淹到了水生的脖子。水生沉到了沟底,一会儿后又浮出水面。水生说涵洞的口不是石头堵住的,是闸阀,闸阀被铁链锁在一根铁柱子上的。
二狗一边颤抖一边说,把锁撬球掉。
水生说撬锁不行。撬锁就像撬银行一样是抢;直接撬闸门,就只算偷。水生叫石匠说,拿铁棒来给我试一试。水生拿着铁棒后又一次沉到水底。在汹涌湍急的水底是不好施展的,但石匠用的铁棒一头是扁的,另外一头是尖的。水生就用扁的那头慢慢的拨动闸门,但没有缝隙,水生无法把铁棒扁的那头插进闸门。弄了几分钟,水生浮出水面来换气。换了几次后,水生说,这水太冰了。怎么这么热的天气水还这样冰?有人解释说,这是水库的底层水,肯定冰。水生说,哪个下来换我试试,我实在支持不住了。可没有人说话。水生也知道其他人下去都要被水没过头顶,更不好换气的。水生身子有些发抖了,但水生咬着牙坚持着。水生用铁棒扁的那头使劲朝闸门底部砸去,闸门被撬了有一个缝隙,水生把铁棒插进缝隙使劲的撬,闸门才被撬起来。
水生颤抖得厉害,大腿弹二弦,小腿弹三弦,“弹”得连衣服都穿不上了。这时水生才感觉冷得受不了。水生实在支持不住了。
二狗说水生,你回去吧,这么大的水你家田里我们会放满的。
水生在颤抖,但水生却说,没事没事,只要把水放到田里,感冒了也值得。
6
水进田了。水生说各人看着各家的田口子,水满了就堵掉留给另外一家。
小渠边,每隔一小段,就站着一个人提着锄头守护,就像交通民警列队欢迎上级领导或者首长的到来,或者算夹道欢迎,或者属维持秩序。二狗媳妇是什么时候来的?二狗不知道,谁也不知道。
水生说,你怎么跑到这里来了?
二狗媳妇说,你玩的这点狗解溲瞒得住谁呀。你才在翘尾巴,我就知道你要拉屎。
水生说,当时我们真的出去撒尿。
二狗媳妇说,你们走后,我家门口放着的锄头就不在了,我就知道你们要去干啥了。
水生说,是是是,赶快瞧着你家的田口子去,不要放漏掉,看看田埂哪里会漏水,就去堵住。
在黑夜里时间长了,人影在哪儿动,水生是看得着的。二狗家的两块田都在进水,下一块田水都快满了,白花花的水映着田埂边蹲着堵裂缝的二狗。水生说,二狗,别家是一个人来放水,你家却是两口子一齐上。别人家的水还没有进田,你家的一块却放满了。二狗媳妇听着水生骂自己打屙屎主意,就说,水生他伯,我家的秧长的比你家的高了,再栽不上就没希望了。我知道你们是去干啥的,我就来这里等着的了。
水生知道自家秧田里的秧苗不比二狗家的矮,本来应该先放水生家的水,因为水生家的田在沟的上段,现在二狗家在下段的两块田都快满了,而上段水生家的田却仍然干脆了的。但二狗媳妇早就来等在这里了,而且已经放的差不多了。如果按照到水渠的先来后到,水生应该是先到;如果按照到自家田边放水的顺序,应该是二狗媳妇最先到,水生是最后到的。水生没有说什么,就让二狗媳妇先放吧。
水生家的田放不进水去,水生一下就找不到事情。水生站着太冷了,就走动着挨个查看水口子。水生像警官对民警挨个查看警威的样子。水生查看谁家的水口该留多大,谁家的田在中间,路线有多长。水生一边查看一边帮着清理沟道。水生说,都看看给有黄鳝洞,黄鳝洞漏水快得很。有人说水生,你最喜欢堵黄鳝洞,快来帮帮。水生听着他们把黄鳝洞比作了女人的那个,这时候水生冷得牙齿吱吱作响,没心肠开玩笑,水生说不要牛哄哄的了。你们的田水要满了,我家的却还是干垡子。那人说,你要让给二狗媳妇先放怪谁呢?明明想占人家的便宜。水生冷得有些龇了,水生说,你说个球。
7
水生媳妇请村子里自己开诊所的那个既是兽医又可以给人看病的乡医来给水生输液。输完液,媳妇又去请道士先生来为水生除邪。因为媳妇听着水生嘴里一会儿说放水的事,一会儿又学野猫叫。水生说,这就是鬼叫,你听到没有?
道士先生用五谷在水生身上乱打一气,还用辣椒放在火里烧起烟雾,把水生的头强制按到烟雾里去熏。道士先生嘴里念着吉吉如令的咒语。水生的喷嚏又像发连环炮样的响亮起来。媳妇对水生说,神药两解,都试一下,只要能好,管他是怎么好的。
水生有些清醒了,但嘴里仍会讲着胡话,水生叫媳妇说快去放水,快去放水,水已经放下来了。媳妇又怕又气,怕水生一口气不来,剩下她怎么过;让媳妇伤心的是水生去放了两晚上的水,别家的都放满了,只有自家的还在干生生的,更让媳妇生气的是下块田的二狗家的都有水了。这个砍秋头的是整啥子去了。媳妇说你到底是不是去放水还值得怀疑。
水生没有讲胡话了,但汤水不下,病奄奄的什么也做不了。水生坐在梨树脚下靠着树干,觉得身子软软的,头晕乎乎的。水生看着过路的妇女用撮箕挑着码得高高的、圆圆的像小山似的秧苗,嫩绿的秧苗尖交叉着埋在里面,细嫩而又白皙的根须朝外,下面大,上面小,到了最后,秧苗的尖也是站立着的了,整个的像一个洗净了的大白萝卜。
放上水的人家现在可以挑着这种“大白萝卜”悠哉游哉的去插秧了。要是水生家田里也放上了水,水生就像这样走路都还趔趄着,也是要到田里去的;就算水生挑不起秧苗,至少水生也要弯着腰在田里跟着栽秧,拉着绳子把握秧苗的行距、把秧苗栽成一根线的。但水生家的田是没有水的。
水生还老想着放水的事情。水生是带头大哥,是自己带着大家去偷水的。别人就不会这样想,就没这胆量。想到自己还曾带着大家去偷了点水下来,尽管自家田里还没放上,但离沟近的很多家都在插秧了,水生嘴角颤动了一下,心中就有些激动。可水生又在心里骂,这些狗日的顾头不顾尾,有水就朝自家田里扒,没水时一个都不敢带头。特别是二狗媳妇,净打屙屎主意。而就是在放水的晚上,看着水生撬开闸门后水哗哗地淌下去,其他人全部扛着锄头一溜烟的跑到了自家田里,哪个还管水生的死活。水生在沟渠里跳了多少次才扒住渠坝的坎的。水生费了很大劲才爬上来。
水生庆幸终于没有死,但水生没有精神,水生想站起来,可水生没有力气站起来,水生想回到铺上去休息,水生试着站了几次,脚是软的,软软的又蹲下去坐在地上了。
8
水生坐在地上,眼睛看什么都是花的,花着花着,眼睛上端白白的飘着一片“白云”,那白云飘啊飘的,一会儿就飘到水生家门口了。水生家门口的一条小路,基本都只有手推车拉东西进进出出,从来没有过机械车进来。当那“白云”的面包车飘到自己面前的时候,水生才看清是辆车。开车的人技术真好,这样的路都能够进来。
水生被抓走了。水生坐在车背后,前面一排坐着一个水库管理局的,还有一个村支书。最前面,驾驶员是派出所的,和驾驶员一排的那个,还是派出所的。
水生在车上,是被拉着从自己家那干垡子的田边经过的。从茶色玻璃的车窗望去,水生仿佛看着自己家田里是有水的,那水是从天上来的吧。水清亮亮的在水生家田里荡着波纹,很快就可以把干垡子泡软,泡软后的田垡子幸福地倒在柔软的水里,田里就白茫茫一片水,水生家田里就可以插秧了,水生的眼前一会儿就变成了秧苗,而且秧苗也和其他家的一样,绿油油的,在南风吹拂下不住地、一排排地向一个方向点头,点着点着,就变成了沉甸甸的穗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