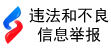杯子(一)
来源:昭通文艺网 更新时间:2009-03-20 13:57 作者:夏天敏 责任编辑:
一
“两个月,两个月……”他重重地叹了口气。桌对面的那人在改稿,没听清他讲什么,只抬起头,从眼镜的余光里看了他一眼,又低下头去了。
伏案写了几行字,他心中又一阵焦虑,一阵惆怅,心里空落落地,有着无依无凭的感觉。房子是新房子,墙壁自得晃眼,而下半截的墙,又绿得忧郁。他家的墙呢,有年头了,房子又漏雨,就写了许许多多的内容在上面。他爱独处,爱遐想,就看那各种各样的污迹,就看出许多名堂,就成了一本童话集。一看那些图腾似的污迹,他就恍恍惚惚,飘飘曳曳,神思飞扬,其乐无穷。怕回到现实,一离开这些肮脏的咒语似的污迹,他就不能自持,变的没有自信,谦恭卑微。在这间整洁、堂皇、肃穆的办公室里,他经常有一种惴惴不安的感觉,他轻轻地走路,轻轻地说话,轻轻地抄写稿件,时刻在考虑和主编副主编讲话时脸上应该有种什么样的表情,笑应该笑到什么程度,手应该怎样摆放。他也常常为走进主编办公室颇费脑筋,主编在和人谈话怎么办?主编和别人发生争执怎么办?主编副主编有矛盾,对他们的笑是否应该一致?如果有区别,那种细微的分寸应该怎样掌握而不被他们发现并且双方都满意?如果主编为什么事发脾气能不能争取把微笑贯彻始终?主编打喷嚏应不应递去手绢,但他会不会嫌弃,如果不递去他又没带岂不是就有些不大雅致而迁怒于我?他就为这些事常常伤透脑筋,他活的不引人注目但又十分疲倦,他外表冷漠内心炽热,思维活跃脱离轨迹。他看办公室的白墙就忧郁,最初看时是个立体的面,组成个框子,将他置于其中。再看就无,就白茫茫一片,时空消溶了,剩了渺无涯际的空虚,人就变成一片小小的落叶,无休无止地飘落。那种没有依凭的失落感,像毒液一样漫延他的全身。这白的虚空,是忧郁、悲哀、惆怅、孤独的组合。
“喂,抄的怎样了?”那人问他。
又回到稿子上,又抄,笔倒是沙沙响,他却感到是滞涩的。
“两个月……”不知怎的,他咕咙了一声。
这回是听清了,那人问:“啥两个月?”
他没答。那人说:“发神经!”
这是一家地区级报纸。
他来这里上班已经四个月了。他原是一家工厂的工人,时下工人是不能进行政部门或者事业单位工作的,他却像模像样的有了张办公桌,像模像样的帮别人改稿,还像模像样的在他编的那报上签字。第一次在版面上签字他的手抖得厉害,那歪歪曲曲的变了形的字像心电图的曲线披露了他的心迹。他能到报社上班,那消息深深地震撼了那些认识他的工人。就好像一个叫花子一夜成了百万富翁,一个还在高原上放牧的人被接到联合国当秘书长一样不可思议。连接到通知的厂长也怀疑它的真实性,叫秘书打电话问是不是弄错了人名。因为他在那个厂委实没有什么能引起注意的地方。不要说个子高大人又俊美,或者在技术上有它一手,或者在蓝球场上跳跃腾挪、球艺超群;或者有副金嗓子,在厂宣传队独压群芳;再不济,也身强力壮,会那么几套什么拳,在哥儿们中称王称霸,他什么也不占,连身材也是既不高也不矮样子既不英俊也不丑陋,人们常常忘记了他。厂里给单身职工换房的时候,他明明站在人圈里人家也忘了他,以致他抱着铺盖在走廊里徘徊的时候,宿舍管理员才发现自己的疏忽。他住的是五人房间,他睡在角落里没人愿睡的床上。他无事就躲在里面。
可他确确实实到报社了,当然是合同工,六个月。只有他自己知道他能到报社的秘密。这个地区是有办报的历史的,那场浩劫中中断了。不知怎么回事,他家会有一本土黄色的、营养不良的、皮肤皴裂的旧报纸。那报纸上的字是患了近视眼的瞳孔,迷迷瞪瞪的看着你,就这么一本旧报纸,竟使得异常孤独的他常常废寝忘食、细细揣摸、慢慢赏玩。于是鬼使神差,他在他的幽居独住的洞穴里萌生出向地委写信恢复报纸的想法。那段时间在闹地震,哥们趁着机会就不上班,变着法儿玩。有到很远地方打野鸭的,有搭伙钓鱼的,有成天甩扑克的。这些都无他的份,他在家里的那间小阁楼里很无聊,就写信,还写起兴头,一连写了十来封信。每封信都好几千字。震期过后,工作秩序正常,他的信摆在地委办公室的桌上已经一大堆。那书记看了一封,就为他的精神感动。书记也是舞文弄墨出身的,不时有短文见诸报端。心想地震期间,如有一张报纸,不知可载多少感人事迹?于是就开会,就拍板,就拨款,就委人筹建。于是就出来第一张报纸,就将他的信转给报社,作为资料保存。
主编看过他的信,萌生出一个愿望,想见见这位具有远见卓识的人。主编仕途不顺,正当着红红火火的宣传部长,却突然让他出去休养,回来就赋闲。正好筹办报纸,捡了主编当当,心下也有些感激写信的人,按写信地址找他面谈。去了,主编先是失望,后又觉得他忠厚可爱,不像时下年青人,巧言令色,轻薄骄狂。便答应让他来试干半年,按流行办法订了合同。
他感到了自己的价值和尊严,他真想哭,真想痛快淋漓的哭。他记得大家注意他除了这次以外只有过一次,那次被人注意是付出了代价的,他住了半月医院,还扣罚了半年奖金。
那是一个大好的天气,球场上围了许许多多的人。那些人又都极兴奋,仿佛每个人可以领到一个媳妇似的。他虽然孤独惯了,也禁不住那火辣辣叫喊的诱惑,他贴住人圈,后来却被挤进了,他看见人圈中摆着两张拼在一起的乒乓桌。铸工车间的一个哥们蹲在地下用手托住腮,他身边是张半旧的单车。有人说:“王三毛,就是一句话,你是站着屙尿还是蹲着屙尿的,蹲着屙尿的就算了。”原来王三毛跟哥们赌嘴,说他敢在两张乒乓桌上骑车,赢了,输他一封沙糕。几个哥们来了兴趣,就在俱乐部抬了两张乒乓桌在球场上,抬来了,这老兄却草鸡了。虽然话刺激,他却不为所动。有个姑娘脸皮厚,说:“吐出的话泼出的水,给收得回去?我吐泡口水你吃掉,就算了。”王三毛兴奋的脸发红,“嚯”地从地上站起来:“你吐,你吐,我张口接着,正想尝尝姑娘的口水,你倒知情解意。”那姑娘虽然脸皮厚,也吃不住劲,忙缩回人丛中去了。
他弄不明白自己怎么就激动了,他也不明白自己怎么就想起去骑那单车,也许是潜伏在深层意识里的被压抑得太久的似乎是人人都具有的表现欲猛的冒出了头,他才叫出“我来骑”时人人都感到困惑和惊讶。就有人揶揄他:“旁边蹲着屙尿拌泥巴玩去,充什么能!”他也就觉得是有些不大对劲而准备退堂,也就有人怂恿他“好歹长着个把把,站着是条汉子,骑给他们看。”他看着有这么多人在盯着他,被这么多人注意也不容易,骑得好了会有人欢呼,即使跌在地上,也会有人惊呼,这么多人中,还有不少姑娘呢。他吼一声:“我来上!”又悲壮,又沉雄。众人“刷”地让了道,又有热心人将车抬来放在桌上。
两张乒乓桌的长度和宽度不用说也能想像出来,他才抬脚,就得用“如临深渊,如履薄冰”的词来形容了。身上的汗是一层层出来,脚像踩在棉花上,正犹豫、正恐慌、正后悔,下面声音潮样涌起,见人来得益发多,还有人朝他挥帽子,就涌起自豪感,就满足了心底的一种什么需求。于是就骑上去,就将车骑成牛撤尿,歪歪斜斜的,才几步,转不过弯来,连人带车就跌在桌下了,车就骑在他身上,云山雾海不知所以了……
那次他住了半月的院,罚了半年奖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