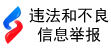水塘子
来源:昭阳信息网 更新时间:2011-03-11 09:29 作者:文章来源:昭通文学艺术网 责任编辑:
一
马儿走时对我说,就这样吧,每天晚上我们就以这种方式会合。马儿的话,我不得不听,他对我说的话就像他爹在村子里对村子里的人说的话一样,有着权威性。
今天不知是怎么了,时间好像跑得比往日要快些。我家里还没有吃饭,但是天色看上去已经暗淡了下来。我心里一直都很猴急,我怕马儿快要来喊我了。
我正在吃饭的时候,就听到在我家的房背后传来了猫叫声。我的心就开始痒了起来,接着紧缩了一下,我知道猫叫到第三声时的后果。如果猫叫到第三声了我才出去,就该吃一口浓浓弥漫着咸腥的痰。
其实这个声音如果仔细听是不像猫的,但大人也不会留意,这是马儿留给我的暗号。我赶紧把剩下的饭全部扒进了嘴里,边嚼边跑了出来。我才跑出我家院子的时候,但他的猫叫声已经叫到第三声了。我刚跑到他身边,马儿就对我说,张开嘴。我说你叫快了,你故意的,正常的叫法你最多叫到第二声。马儿没听我的理由,平和地又重复了一句,张不张?我说不张。马儿变了脸,白了我一眼冷冷的说了一个字。好!接着他猛吸了一口烟,闭着嘴,鼻孔就变成了两根烟窗,烟子浓浓的朝两根烟窗里喷了出来,匀匀的两股,袅袅的上升,开始朦胧后就虚化。我呆呆的看着他。我不知道他接着会怎样,通常他只要把烟吸了从鼻孔里出来,他就要对我加砝码了。但是吃浓痰也太脏了,我想着就有些恶心,我宁愿受点其它的惩罚,我就一直没有张开嘴巴。我不敢正眼看着他,只得偷偷的看着他呼出烟子的虎样。他愣起了眼睛又白了我一眼,看着我紧紧闭着的嘴巴,他把头一甩,说,走,先去喊友尔再说。于是,我就跟在他身后朝着友尔家的方向走了去。马儿走路很快,让我觉得有些神秘也有些后怕,我老是要小跑才能跟上他,我也说不清为什么这样,我只觉得那种感觉有些玄乎,就像他爹给我的印象。
马儿的爹会使法,在村子里是出了名的。不管哪家讨亲嫁女,死人抬丧,都要请他到场,看吉利的日子,以望后来兴旺发达。村子里的人是亲自见到过马儿的爹做法事的,他能把一个用火烧得红通通的犁头套在光脚板上,火红的犁头和脚板一接触,烙得滋溜滋溜的响,烟雾四起。看的人瞠目结舌,都为他捏着一把汗,这把人烧伤了咋办,主人家不是惹祸在自己头上?但是马儿的爹把犁头脱了下来时,脚板一样的完好无损,连点皮肤也不会破。特别在舔火钳的时候他自己舔着没什么,倒把看着的人舔得骨头酥嫩嫩的,毫毛倒立。他可以把烧得通红的火钳用舌头去舔,像一条饥饿的狗得到一块沾满油腻的骨头舔得津津有味的一样,也是舔得烟雾四起,过后也照样不伤什么,嘴里依然吐痰嚼东西依然说话念咒语大声骂人。村子里的人都说,马儿的爹神了,马儿的爹有法,法力无边。最让人们佩服他的是他看的风水宝地,村子里的老人死了,凡经他看过的地,后辈人和家里的牲畜一年四季都顺畅,家业也就渐次发达起来。村里的人对他很是尊重,敬佩,见到他就要老远的笑起来,主动和他打招呼,没人敢得罪于他。
对于马儿,我也是不敢得罪他的,就像村子里的人不敢得罪他爹一样。我也不知道今晚到底是怎么了,一路上,我说不出心里是一种啥滋味,总是感觉空落落的。去友尔家的整段路上,我就跟在马儿的身后一直小跑,没有说话。
二
我和马儿到了友尔家。我们每天晚上都要相约着在一起玩的,所以每天我们最希望的就是天快些黑下来。友尔是个最自由的人,家里只有他爹和他。他出入都很方便,因为他爹也很少会管他。我们走进他家里还没有坐下,友尔就说,走了。我们才走出门口,马儿就说,他爹今天晚上要在家里做法事,还要烧鸡蛋,他爹不准对外人讲,这是他家里决定的一件大事。马儿又说,他爹在村子里看着一块真正的风水宝地。马儿还说,他爹和其他家看的风水宝地都不是真正的风水宝地,都是留得有一手的。友尔说,那我们今晚就不能去你家玩了。马儿说,可以去,但是不准对任何人说。他爹说了,不准让大人们知道,童子娃娃可以,但是也不是全部都可以,要和他玩得很好的。才放心。我想,这样就很好,因为我早就想看马儿的爹亲自做法事,还有马儿也不会再吐浓痰给我吃了。我正在这样想,接着马儿就指着我对友尔说,他学猫叫到第三声了我才出来,没有吃他的浓痰,这是早已就规定的,如果不吃浓痰就不准我去他家。我有些失落,我想不到他会给我这样的惩罚,对于马儿他爹做事的神秘、稀奇的一些方法我是非常想见到的,我觉得就像看魔术表演一样的过瘾。但是要吃一口浓痰,我又极不愿意。我无助地看了一眼友尔,友尔也正看着我。友尔说,你爹经常都要用烧纸烧鸡蛋的,算了,他没有吃浓痰,到你家不要分他你爹烧的鸡蛋给他吃就可以了。可能马儿觉得这个主意好,就说,要得。我高掉着的心一下子才落了下来,很讨好地走在了他们的后面。
还没到马儿家的时候,天比先前更黑了,我觉得四周都是黑沉沉的夜气。我们的村子很大,是因为房屋稀稀疏疏,建得不密集。但此时的村庄是一个整体,不再像白天看上去有些分散,村庄在黑色的天幕下像是伏卧在群山中的一个动物。偶尔有风从远方刮过来,白杨树叶抖擞摇摆,发出一浪一浪的声音,哗啦啦的响着,就像水一样的流淌。不时有几声幽幽的狗吠声从黑暗中传出来,声音很长,就像村子里的一些老人唱送葬歌的调子。我们走在村子里,黑夜渗透了整个村庄,把整个村庄都淹没了,每家的门都紧闭着,偶尔有灯光从不严实的门缝里跑了出来,它们也可能想跑出来玩玩,也想跑很远,但却被黑夜挡住了去路,出门缝不远就死死的贴在地上一小段就看不见了。
我们进了马儿家里。推开门,我就看到在他家的供桌柜上点着两支蜡烛和三炷香。在三炷香上面,青烟缭绕,缓缓上升,浮在楼顶上正在向周围扩散着。整个房间里弥漫着一种神秘莫测的气氛,马儿的爹在嘤嘤嗡嗡的念着什么,含混不清,带有一种摄人的魔力,在寂静而肃穆的空间,来回飘荡。我们轻轻悄悄地坐到了火炉的角落边,马儿的爹念一会儿又比画一会儿,末了,长长的嘘了一口气就停了下来。笑眯眯的望着我们三人
马儿的爹和我们坐在了一起,围在炉子边。我们整整齐齐的像是他的三个儿子。马儿的爹意味深长的对马儿说,实际也是一同对我们三个人说,你们都已经十多岁,是些老大不小的人了,不能一天放了学就在村子里游手好闲的了。他看了看门,门是紧闭着的,他又把目光移朝我们这里,声音放得很低说,今天晚上我要为村子里做一件大事。我们盯盯的看着他,精神高度集中,就像在课堂上等待老师讲一个精彩的故事一样。他顿了顿,特意的看了一眼友尔,显出一副长辈特有的慈祥和关怀,他对友尔说,侄儿,你知道你妈为什么死得这样早。友尔听了这句话,神色立即就暗淡了下来,他没有什么准备,马儿的爹怎么会突然问起这样的问题。这句话就像一个突发事件一样,让你来不及痛苦,也来不及反抗。马儿的爹这句话是一盆水,把友尔的全身都泼得冰凉,把眼睛也打湿了。我看到打进眼里的水变得灼热,把眼圈都烧红了。友尔没有说什么,只是摇了摇头。马儿的爹看着友尔的神情,叹了一口气说,就是我们村子后面那个深水塘把她克死的。他慢悠悠地说,我看过了那块地,那里从地理风水来看,中心以村子的道路为界,北面临山,地气较足;南面临河,水财为多。后有五莲山依靠,塘里的水深入地脉,水势宽阔,很好。两边又有群山叠伏,来龙深远,地气十足。马儿的爹说到这里,顿了顿,端起杯子喝了一口姜开水,接着说,你们都学过了地理,从天文学的角度讲,它包括大气层与地球水流的相互流转,是一块真龙宝地。但是,每个人与生俱来的先天基因不同,命理不同,而你妈恰恰不适合于她的生命态势,这个水塘同她个人的命理五行不相配合,所以她就被克死了。马儿的爹又喝了一口水,很慈善地对友尔说,如果这个塘子依然存在,那对于整个村庄特别是对于你家是极为不利的。友尔听了一下就来了精神,急不可待地说,那我们就把它填掉。马儿的爹脸上的肉横了一下,脸皮上露出了一丝笑容,但又不像是在笑,只一下子就不知去向了,这让我更是感到他的神秘。马儿的爹好像自言自语,又重复了最先说过的一句话,今天晚上我要为村子里做一件大事。友尔似乎还想说什么,我看到他的嘴巴动了几下,但没有说出来,好像喉咙被什么东西堵住了。
我有些不理解,之前我就听马儿的爹对马儿说过,村子背后那个水塘子才是一块真正的风水宝地。要是埋下一个人,对他家很好。这时,他爹怎么会说对友尔家不好呢。
三
对于友尔来说,他已经失去了母亲,这个家再发生些什么事,这是多大的不幸。
我看着马儿家供桌柜上三炷香的青烟,忽飘忽散,我的脑海里全是些惊魂未定的东西,我感到周围凉飕飕的,那忽飘忽散的青烟就像幽灵在到处移动一样,使我呆若木鸡。我们一个也没有说话,很显然,村子后面的水塘子要被毁掉。但我感到迷惑不解的是,村子里这么大的一个水塘子的事情,为什么只能让我们还没有结婚的两个外人知道呢。我正在这样想,马儿的爹好像真的会算命一样就算到了我的心思。他看着我又笑了一下,接着又和我们解释了一大通高深莫测的道理,而脸上一直都挂着笑容,那笑容随着他的说话,久久的浮在他的嘴唇上。马儿的爹说,在一个村子里选择修房住宅,最重要的就是要选房屋修建的地理位置及地理环境。我只模糊的听清一些直白的话语,他说的什么几千年的传统风水来看,住房必须要依着什么山了水了,风了气了,北了南了的。我们一点不懂也听不懂这些东西,他又接着说什么有靠山,地气,之类的话,还说一些什么左青龙、右白虎,我一点也认不得,我听得云里雾里的。我听得明白的一句话就是他说我们的村子后面靠着的不是山而是一个水塘子,这就是不好,如果这个水塘子要是生在村子的前面就是最好的了,那村子里就会很富裕。
马儿的爹这么一说,我也就有些怨恨起那个水塘子了。友尔也一样,在他心里不仅是怨恨了,我看他显出一副苦大仇深的样子。友尔的目光从开始的痛苦变成了一种哀求的神色,盯盯的看着马儿的爹。马儿的爹却没有说话,而是又端起了杯子喝了一口姜开水,微笑着看着友尔。友尔坐不住了,他说,我回去叫我爹今晚就把它填了。马儿的爹一听友尔要去告诉他爹,他的微笑一下子就扩展到满脸都是僵化了的笑纹,他不再喝水沉默着了,把杯子放在地上。他斩钉截铁地说,这件事不准和任何人说,为什么只有你们两个娃娃知道,那是全村人都在用的水塘子。洗菜。洗衣服。牲畜饮水都要用的。你去填了,全村人能饶你吗。马儿的爹又对着友尔说,还有你爹是不相信这些东西的,要是相信,你妈也就不会死了。他又喝了一口水接着说,你还在很小的时候,那时你妈还没死,村子里的王五保户死了,我就说要把她埋在这里的,全村人开始都同意我看的坟地,当时就只有你爹一个人不同意,后来就有很多的人也就不同意了。为了那件事,你爹和我现在都还在没有讲过话,我是为了这个村子好,我看你也不像你爹,和马儿这样好玩,我才和你这样说。友尔显得急了,语无伦次地说,那咋,咋办。马儿的爹又恢复了原先的神态,嘴角上又露出了笑容说,我已经想好了,但是要你受点苦,看你给愿意。友尔一点也没有考虑就说,愿意。愿意。不知为什么,我感到马儿家整个屋子里都是奥秘,到处都若隐若现的漂浮着一些捉摸不定的影子,我有些害怕了,但我不敢说,还有马儿也再不时的望着我。就是让我想说或者叫我说我都不敢说了。马儿的爹笑了笑又说,村子里的一部分人是同意把这个水塘子填了的,从去年到今年已经淹死了两个小娃娃了。这个水塘子小孩好下去洗澡,去年曾二家的曾毛毛是下去洗澡淹死的,今年黑发家的三狗也是下去洗澡又被淹死了。这个他不说我也知道的,这两个人被淹死的时候捞上来,我还亲自跑去看的,两个从水里捞上来时都是圆鼓鼓的肚子,就像我们体育老师拿给我们玩的皮球一样。但是这时马儿的爹这么一说到他两个的死,我感到更是一种深不可测的恐惧,我听了浑身都起了鸡皮疙瘩,感觉到后背上蹲着一个幽灵似的。
此时可能大多数的人家都睡了,村子中显得一片寂静,只偶尔有几声狗吠声传向黑夜里。马儿的爹站了起来,打开了一条门缝,夜色墨一样的铺在门外边,他向外看了看,然后把门关紧,又看着我们笑了笑。我被他看得很惊惧,此时我感到他的笑像是在呲嘴,对什么东西很仇恨的样子。他看了我们一会儿,又看了一会儿,接着他又看了一眼供桌柜上的香,三炷香已经燃到了根部。对于他做的事我一向都认为神秘莫测的,不知他要做的事是否要对我们怎么样。他走了过去,弯了一下腰,直了起来,接着抽出了三炷香点燃。回过头来,对我们慎重其事地说,从现在开始,已到了子时。他指着友尔和我说,你们两个去守候在村子后面的那个水塘边,直到卯时才能离开。我不知道卯时是什么时候,我就问了一句,卯时有多久。马儿的爹说,天快要亮的时候。我有些迟疑,但友尔显得很坚定的样子。马儿的爹用烧纸烧了九个鸡蛋,在烧鸡蛋的时候,他又从供桌贵上抽了一炷香,用香拨弄着烧纸和鸡蛋,燃烧过的纸灰不断的往上飘飞,像黑色的铜钱。
马儿的爹把九个鸡蛋平均每人三个的分给了马儿、友尔和我。看着我们微笑着说,这是我开过光的了,你们吃了一切都会顺利,久长久远,快长快大。借着灯光,我看到马儿的爹的笑容很古怪,有着一种看不起,或者是正在想着一件什么愚蠢、可笑的事情。我说不清楚,反正从他整个脸部上长着的一双细眼睛,长鼻子和胡须围绕着的薄嘴唇,都好像要大笑的样子,每一处都包含着笑的欲望。
四
我和友尔从马儿家里走了出来。外面黑得要命,近处什么也看清楚,只见四周的山像是朝我们压了过来,我感到一种从未有过的害怕,就睁着眼听黑暗里的风声。我才想转回家,我扯了一下友尔的衣服,随即我就听到了一声猫的叫声。我突然想起马儿不给我鸡蛋的,我的心思全部集中到了三个鸡蛋上,我反而对黑夜不再感到恐惧。这时,令我心里感到最害怕的是马儿。
我和友尔就坐在了水塘子的边上,周围是黑黢黢的山。马儿没有跟着我们了,我又害怕起黑夜来,每一片树叶落下的声音都让我毛骨悚然。我一直把三个鸡蛋捏在手里,但我始终不敢吃掉。我怕马儿,我怕我吃了鸡蛋马儿又要叫我吃浓痰,或者又会对我怎么样,面对着马儿,我始终不敢对什么自作主张。友尔倒是已经吃了,我听到他拨鸡蛋壳和嘴巴里咀嚼的声音,让我听得直淌口水。他问我怎么还不吃,我说吃了马儿不饶我,他说他都已经吃了两个了。过了好一会,我们都没有说话,但是他的第三个鸡蛋我也一直没有听到他吃,或许他不想吃了,或许他认为一个人吃而我又没有吃,好像又有些折磨我,或许他要故意留着。我正在猜想着,我就听到了一声猫叫,这是马儿叫的,我一听就可以辨得清晰无比。我才要喊马儿的时候,他已经跑到水塘边先说话了,鸡蛋吃了吗,并把电筒照到了我手里白亮亮的鸡蛋上。我说,我的还没有吃,友尔倒是吃了。他又把电筒照在友尔的身上,友尔手里还在捏着一个鸡蛋,但像是睡着了的样子,眼睛紧闭着,两条腿卷缩着,还有一只手紧紧的抓着鸡蛋,嘴却张得老大。马儿把电筒光移到了别处。
我想,友尔怎么啦,他是吃饱了睡着了吗?
马儿的到来使我又消除了对黑夜的恐惧,此时,风又吹得白杨树哗啦啦的响了起来。我喊了一声友尔,又喊了一声友尔,但是他没有回应。他怎么会睡得这么沉,我喊着喊着声音突然变了,我突然想到他会不会是死了。我一下子吓得哭了起来,连再继续喊我都不敢再喊了,我对着马儿哭着说,他怎么了?他不会是死掉了吧?马儿没有回答我,他叫我不要大声说话。我又想要是友尔死了,他怎么没有呻吟,没有哀号,没有一点点挣扎,还有刚才我都还在听到他吃鸡蛋的声音。我跑过去摇着友尔的身子,但他还是没有醒,我想起了鸡蛋,我想起了马儿的爹神秘的样子,我想起了马儿说他爹要为村子里做一件大事,不让外人知道,只喊友尔和我。马儿很愤怒的对我说,不要再摇了,你摇不醒的。我发疯似的揪扯着马儿,我想趁着恐惧还没封住我的嘴之前,我要在这黑夜里大声的问马儿,你怎么要害他。可我当时没有了声音,任我努力的呼喊,却就在嗓子里大叫,声音一点也传不出来。马儿死死地向我按了过来,他扑得太快,我无法自卫,也无法躲闪了。我被他紧紧的摁在了地下,连动一下的力气也没有了。但是在我的脑海里,有一种原始的癞皮精神一直洋溢着往上不断的升腾,我想我必须活下去。我努力的挣扎,我的手刚挣脱出马儿的手心时,我的后脑勺却被重重的碰在了地上。
很久,我感到有一个东西一直扑在我身上,接着我听到从水塘子那边飘过来一个声音。那声音从远而近的飘进了我的耳朵,我听不懂在念些什么,只听到又是什么西了东了,虎呀龙呀,山了气了的。那声音飘到了我身边的时候,我听出了是马儿的爹,他还在念着,前面,开阔……我没有听清楚后面说了些什么,我就听到了一声扑嗵的水响。此时,马儿一把把我扯了起来,恶狠狠地说,这件事不准对任何人说,要不然这时你也就下水去,在阴间和友尔做伴。这时,我脑子里一片空白,我不敢说话,任马儿揪扯着我。马儿使劲的又扯了我几下说,听到没有,他的声音不大,但是很愤怒。马儿的爹走了过来,马儿照亮了电筒,我看到马儿的爹两只手的手指相互交叉着,扭去扭来的,而且在不断地重复着这个动作,像是要把两只手的手指连接一起似的,他的嘴里也在不住的念叨着什么,但我什么也听不清楚。我不知道他走到我身边要使用什么法,我心里很害怕,这时面对着死去的伙伴,我更怕的是马儿的爹把鬼魂附在我身上,还有我自己的生命此时也控制在马儿手里。我正茫然的看着马儿的爹,他却把手伸到我头上摸了一下,对马儿愤怒的说,放开!然后微笑着看着我,问我相不相信鬼魂。从他口里一说到鬼魂,我的汗毛都感觉湿了起来,我不住的点着头。马儿的爹说,相信有鬼魂,那这件事就不能对其他所有的人讲,要是讲了,那鬼魂就自然跑到自己身上。而且是心里一定要随时记住不能讲,鬼魂才不会上身。马儿的爹还说,他的咒语很灵,他可以把病了的人念好,也可以把身体好着的人念病。我用乞求的眼光望着马儿的爹,不住的点着头,我心里一直铭记着,不能对任何人说起这件事情。
马儿和他爹亲自把我送到我家的院子门口,我轻轻悄悄的就爬到我家猪圈的楼上去睡了。我感到我也在水塘里,我的身体上全部是水,湿漉漉的。我不住地乱抓着,挣扎着,漂浮了起来,又沉下去,一刹那,我似乎觉得无边无际的水还带着泥土再不断的像我压了过来,我忍不住哭了起来,我大叫一声。我睁开了眼,母亲正在用毛巾擦我的脑门,我周身都是汗水。我舒了一口气,原来我在做着梦。当我真正清醒时,我看到外面白亮亮的,阳光很好。
五
从此,我再也不敢出门去,也不敢再和马儿在一起玩。我只听说村子后面的水塘子一夜之间就被填了,填了高出路面很多,上面还有草坪,像一座小山。村子里的人传得沸沸扬扬,说友尔莫名其妙的夜间跑到水塘子里去泡死了,村子里的人只感到奇怪。整个村庄都笼罩了一种神秘的气氛。
接着,村子里发生了一些怪事。马儿家妈生了个三胞胎,说是第一个才生出来就长了牙齿,接着第二个生出来就会笑,第三个生出来就开始在地上跑了起来。马儿认为他妈生的这三个娃娃,不是他的弟弟,是怪物,就和他爹一起把三个娃娃打死了。马儿的爹眼睛也突然看不见光了。从此,整个村子里的鸡也不叫狗也不咬。
村子里的人都在惋惜,说友尔夜间跑去在那个水塘子里跳水淹死。其实,友尔怎么会去跳水呢,但怎么死的这个秘密,我从不敢说,我只有让他们不断猜测的一颗颗心灵丧失希望,我也知道我这样做是在犯罪。但我又能怎样呢,我害怕马儿,害怕马儿的爹神秘的咒语,害怕鬼魂。还有马儿现在书也没有读,马儿的爹妈什么都将就他,他在家里想怎么样就怎么样,在村子里也变成一个十足的无赖,马儿的爹眼睛也瞎了。我想他们这样活着比死去的友尔更痛苦。
六
夕阳已经快要掉了下去,黄黄的,像马儿的爹烧了剥开的鸡蛋黄子。我看到了马儿的爹,他之前肥胖的身体变成一副瘦弱的身板,在夕阳的照射下显得单薄无比,像一张他烧鸡蛋用的烧纸。他的影子被蛋黄似的夕阳拉得瘦长瘦长的,掉在了路边的田野里。他手里拿着一根电筒粗的木棍子,棍子在他的前面不住的指去点来,他的脚也就跟着棍子的指点去挪动。我看到他手里的棍子指着生硬的路面停下,他的脚步就向前动了一下,棍子在动着的时候,他的脚就停在生硬的路上。就这样,棍子不断的动着停下,又动着又停下,他的整个身板也就随着一双不太灵便的脚移动着。他手里的那根棍子就像他当年在指点村子里的人在办理死人抬丧的事一样,具有着指挥力,威摄力。马儿也在村子的大路边站着,嘴里叼着一支烟,把手背朝后面,无所事事的抬着头看着天边,一副百无聊奈的样子。马儿不知是惧怕他爹还是什么,见到他爹慢慢的朝他这个方向移了过来,他慢腾腾的就隐藏进村子里去。
我走到了马儿的爹身旁,我想很快的走了过去。我走得很轻,没想到他还是听出有人从他身边走了过去,他停住了手里的那根棍子和脚步,把头抬了起来。他转了转两颗白得像云朵的眼珠,说谁走路这样轻巧,就像风一样,像幽灵一样。我一下子就不敢再往前走了,我停了下来说是我,是我放学才回来。他听出了我的声音,一只手拄着棍子,一只手很快的拉着我,嘴里不停的说,友尔有一天晚上夜间跑去跳水淹死了,你看着他跳的,你知道的,你知道的,他是自己死的。他说完了这句话,然后轻轻的把手缩了回去。我看着他嘴皮不断的抖动着,不断的叹了会儿气,嘴里又嘤嘤嗡嗡的念着不知是什么,自个儿摇着头又跟着棍子向前走了去。
听村子里的人说,每天晚上,马儿的爹都会半夜三更的爬起来念咒语,说友尔自己跳水死去。
从此,马儿的爹每天傍晚都要走出村子来,就用那根棍子指引着自己,走在村子里那条布满石子和牛蹄印,坑洼不平的路上。这条路也是我放学必须经过的地方。但从那一次以后,我再也不敢单独从他身边走,每天放学,我都要叫父亲去接我。
那天放了学,父亲一直没有来接我。我走到那条路上时,我又看到了马儿的爹在路上晃动。我就停了下来,坐在田埂边,想着等他走了回去我再走。可是,夕阳都已经从山顶上消失了,他瘦削的身板依然还在路上晃动,并且他还迎着我从村子的反方向走了过来。
天色渐次的暗了下来。这时,一些小孩已经吃了晚饭跑出来玩了。马儿的爹走到了一个岔路口,没有迎着我这边走,从另一条路走了去,那条路却是通往另一个村庄的路。一群孩子跑到了他身后,嘻嘻哈哈的对他说,老者,老者,是不是要回家,回家的路在这边,在这边。马儿的爹只听着周围都是孩子们的声音,在原地转了几个圈,他还是找不到孩子些说的这边是在哪里。这时,天地间灰蒙蒙一片,他看不见的太阳已经落尽,但是他肯定知道时间也不早了。他听了孩子们的话,但是他连自己从什么方向走过来的他都记不清了。他朝着孩子们说话的方向走了去。可是,这条路也不是回家的路,恰好与村庄背道而驰,我看到他走的这条路又要走到我们的学校。
看着他移动着的一副虚弱的身板,在晚风中像是要被吹飘的样子,我很想笑,但是我怎么也笑不出。一刹那,我觉得我不再害怕他,我走了过去,拉着他。说,错了,这条路不是回我们村子的。他听到了我的声音,脸上挂上了一丝笑容,他干瘪的脸颊上,我看到一双眼睛眯着,嘴角不住的往上翘,气流从鼻孔里吹了出来。他这次的笑,让我感到一种真实,很苦涩。他拉着我的手颤抖的说出了友尔两个字,顿了一下,又接着说,走走。就走走。
(文章来源:昭通文学艺术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