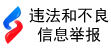父亲・果园
来源:昭阳信息网 更新时间:2011-10-08 13:53 作者:舒显富 责任编辑:
“果园”二字能在我的不同作品中出现,这决非故意为之,而是它与我的生活紧密相关,像一个连锁反应,从父亲到家庭的每一个成员之间,都围绕着它快乐或悲伤。
无论我远离故地,还是守在它身边,果园总是那么亲切,和直入人心。
春日里百花齐放,粉红的花朵钉满枝头,任蜂儿呢喃,任蝶儿飞舞,像一位农家姑娘,朴素中满含羞涩。落花时节,更是风起一浪千堆雪,纷纷扬扬地扑打着全身,甚至一瓣又一瓣地撞击心底,直至夏天、秋冬,仿佛都被这春天占据,一遍遍一年年。
记得这些果树和我的年龄相差不大。1986年的秋天,父亲拿定主意栽苹果树,便带领全家人挖坑、放粪、栽苗、泼水……没想到的是,当天栽下的小树苗在夜里就被人偷掉了一大半,父亲当时很生气。不久之后,父亲又补栽了一些树苗,并把坑挖得很深,防止再被人偷,但因此也留下了后遗症。
时间过得飞快,果树一年一个样的长高长粗了,由试花逐渐到了高产,由追求产量逐渐到了追求品质,市场的价格也发生了变化,这得从果树开始挂果说起。
三年后,果树第一次试花了,我们全家人喜出望外。那种心情像过节一样的,我们随时都想跑到果园里去瞧瞧。父亲更是一心扑在这一亩半地里,忙完了农活,便背操手,去看他心爱的果树。
也是这一年,父亲开始学习果树的种植经验,到处投法取经,学着给果树压条、拉枝、修剪、深翻……还试着疏花和疏果,把树型按他的要求培养了出来。这年秋天,我们家的金帅苹果平均价格卖到了八毛钱一斤,可把全家人乐坏了。虽然产量不高,只有五六百斤,但我们全家还是感到很满足。
随后的几年里,父亲又陆续地在果园里栽了桃树。桃树的结果,也为我们带来了一定的经济收入。可这样一来,只要两三年以后,桃树的长势就要超过苹果树,第四年上就长得高过了苹果树。
开花的时候真是姹紫嫣红,好不热闹,把整个果园开得红艳照人。花开季节我也总是老喜欢到果园里逗留,这里看看,那里望望,闻着清幽的花香,看着鸟儿、蜜蜂、蝴蝶在园子里飞来飞去。而父亲这会儿正在给果树地松土,准备花谢后就立马施肥灌水,有时天干为了找水源,得起早贪黑地挑水灌树,或者冒着炎炎烈日,一次又一次地往返于水塘和果园之间。久而久之果园里踩出了一条小路,至今这条小路还弯弯曲曲地卧在园中,像见证岁月的老照片,又像一段记忆,难以忘怀。
90年我刚好十二岁,外婆的突然离世,像一场春寒席卷了我们全家,全家人都沉浸在失去亲人的巨大痛苦之中。祸不单行的是,就在那一年里由于干旱,我们家的田里也荒废了。父亲急得乱作一团,请人帮忙,发丧,又要想着田地,真是一筹莫展。可父亲还是坚持住了。
四月的天空万里无云,太阳吐着一股火舌直烤着大地。各种树木在开花时节,遭遇了无情的干旱天气。火南风把地皮都吹干了。持续的干旱使果树的花期受到了影响,人们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却又想不出解决的办法来,只能就这样看着,谁也不敢冒然给果树灌水,因为花期灌水会使花受损,严重的话会使花提前凋谢。
花一谢,父亲就像一只领头羊一样带着我们挖塘,施肥,挑水,忙碌了好几天才干完。果树总算有惊无险,安然无恙了。
“农村的事咋个就没得个做的时间,才把果树灌了又要忙田里的,可这旱情哪里去找水呢?”父亲焦心地和母亲商量。
我们家的田是尾水田,要等其他人家放完了才轮到我家,到那时还有没有水都是个问题。这事像一块心病似的搁在父亲的心里,这时的父亲总是一个人独自抽闷烟,那一阵阵的烟雾仿佛在诉说着他的心事。
开闸放水了,可刚放几天闸塘里就没有水了,一看就晓得我们家是放不上水了。父亲正一心急着想办法,外婆却突然去世了,这突如其来的打击,好比雪上加霜。
外婆没有什么亲人,只有母亲这唯一的一个女儿,正是这样外婆才一直和我们生活在一起,操持着家里大大小小的家务,从来没有任何怨言。从我记事以来,外婆在我的心中就是善良而慈祥的老人,我和三姐就是她一手带大的,或许是这个原故吧,我和三姐总是喜欢和外婆在一起,听她讲故事,帮她做家务,有好吃的也要偷偷给外婆留着点。那时我和三姐老是靠在她身边,外婆常常会摸着我的头说:“六儿真听话。”
父亲和外婆之间也情同母子。“我们家里也就全靠你婆婆管着了,要不然怎么能放心的在地里干活,多亏了她老人家。”父亲经常对我们这样说,念叨外婆的好。
外婆的去世,让我们一家人十分伤心,从小就跟外婆焐脚的三姐,眼睛都哭肿了,母亲也是。而正是插秧的农忙季节,家家忙着放水插种,我们家却管不了这些了,只顾着把外婆送上山。平日里父亲就和村里人的关系很好,有许多人还是放下手头的活路来帮忙,有的买菜,有的当厨,有的守夜……前前后后忙了五六天,外婆才出灵。而这些日子,父亲没有一夜合过眼,深陷下去的双眼布满了血丝,人也瘦了一大圈,本来就显得单薄的父亲,这会儿风都吹得动了。
办完丧事后,父亲整个人都累跨了,像生了一场大病,又黑又瘦的脸上,颧骨高高地突起。休息了一段日子才恢复过来,可田里放不上水,彻底荒了。
父亲是一个豁达乐观的人,沉重的打击没有让他停下来。看着慢慢长大的果子,他便把心思花在果园里,从早到晚忙碌,给果树剪枝,施肥,打药,像一头不知道辛苦的老牛,拼命地低着头向前拉。转眼,就进了伏天,果子长势很好,父亲紧锁的眉头渐渐的地舒展了。那一年,是果园救济了我们全家,让我们渡过了难关。
后来的多年里,父亲依旧管理着他的果园,但桃树实在是长得太快了,茂密的枝叶遮挡了苹果树的正常生长,父亲只好忍痛割爱地把桃树砍掉,苹果自然空出了许多位置,受光的条件好多了。其间,父亲还发现果树得了干腐和根腐病,又成天爬高上低地给树治病,把果树当作宝一样地伺弄着。
“这就是哪会儿怕人偷,栽得深了给整的。”父亲看到我在一旁的时候,喜欢和我说这些。
“刮一下皮,再抹上石硫合剂,过一久就会长好了。”
父亲的补救措施延长了果树的寿命。可是一个市场的品质正在酝酿,这是父亲没有料到的事。
新的品种进来了,像红富士,新红星,108果……很快就占领了市场。青皮的金帅价格一下子垮了,又大又好的果子只卖三四毛一斤,有人就建议父亲砍了果树重新栽新品种,可父亲有点舍不得,这可是他花了多少心血栽种起来的果树啊,就像他的朋友和亲人。父亲只好另作打算。父亲在另一块地里种上了新的品种,老树依然留了下来,那会儿有谁知道,我正在读中学,家里不能没有果树,如果挖了重栽的话,至少要五年才会投产,我读书的开销怎么办。父亲总算是作了明智的选择,否则也就不会有我的今天。
一晃二十年过去了,父亲越来越老,头发和胡子都白了。在我们的一再劝说下,父亲渐渐地的很少上树了,有的果树也一枝一枝地渐渐枯死了,每年要摘两万多斤的苹果,也逐渐减少到一万多斤,过些年可能更少。父亲已经是古稀之年了。
“树能活到我过世的那阵,也要得了。”父亲还是很高兴地说。听到这些话的,我深深体会到父亲对果树的珍惜和爱。
花开又挂了一树,花落又飘了一地。父亲又背操着手走进他心爱的果园。花儿朵朵,片片纷飞的花瓣,像如烟的往事和飘逝的记忆,落在父亲的头顶,肩膀和脚下。父亲依旧朝着果园的更深处走去……
(舒显富)